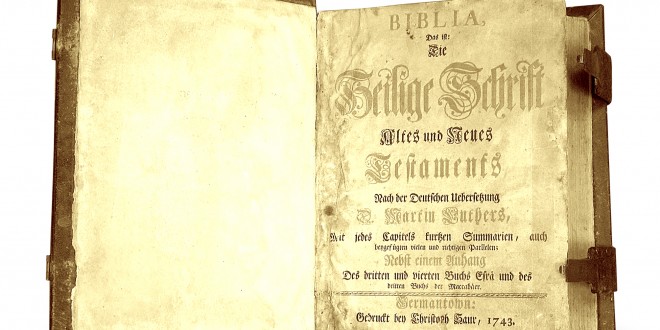文/罗伯特·戈弗雷(W. Robert Godfrey) 译/煦 校/陈彪
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是更正教宗教改革的一个响亮呐喊。这个确认针对的是宗教权威的问题,并总结了更正教的认信——宗教真理可以确切地知道,不是出自教皇和会议,而是仅仅出自圣经。唯独信心(sola fide)、唯独恩典(sola gratia)和唯独基督(solus Christus)的宣告总结了福音的本质,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则指出了此福音所有知识的可靠来源。
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们试图了解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对于十六和十七世纪更正教的意义。最近,他们对关于圣经本质和权威的理解在这一时期的改变与发展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大多数释经家看到,十六世纪的改教家和十七世纪的正统神学家之间的基本一致和延续: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它所说的一切都是绝对可靠的。[2]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一些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多受新正统[3]的影响,强调改教时期和随后的更正教正统之间的不连续性。这个学派认为,当代福音派所信仰的圣经绝对可靠和无误是对早期改教家观点的一个背叛,是从十七世纪正统的新观念里发展出来的。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对改教时期和正统时期之间的不连续性的强调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新的研究表明,改教时期和正统时期观念之间的连续性是很强的,变化的过程要比以前看到的要更加渐进。[4]变化确实有:要回应新的敌人,以更细致的措辞将古老的神学辩论更加精细化,并意识到需要精确的辩证语言。但基本的神学方向仍然是相同的。
本文将说明,最近的研究所表明的十六和十七世纪神学之间的连续性,也适用于圣经权威的问题,正统时期忠实地接受和保持了改教的基本立场。虽然从宗教改革到正统的过渡中,重点有所迁移,并且这两个时期可能对一些批判给出特定的结论,但两者在对于圣经的基本信念上是一致的。对于两者来说,圣经是基督教唯一的最高权威,圣经是无误的。
要在一篇文章中研究两个世纪对于圣经权威的态度,需要设立严格的限制。为此,我将本文限制在批判一本书,会很有帮助。这本书是那些否认改教家接受圣经无误的代表作,他们认为圣经无误的信念是正统的一个不良产物。这本书就是罗杰斯和麦金(Jack B. Rogers and Donald K. McKim)的《圣经的权威和解释:一个历史的进路》[5],它是这方面重要的、需要仔细评估的一本书。罗杰斯和麦金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命题陈述,即,改教家不接受圣经无误。这个论点,必须用十六和十七世纪对圣经权威的态度的原始文献和其他相关二手文献进行考察。
罗杰斯和麦金的论点建立在严格区分圣经功用和形式的基础上。他们坚决主张教会历史具有有说服力的见证,证明圣经在履行其介绍基督救恩信息的功能上是经久不衰、绝对可靠的。但是,他们却否认那绝对可靠的功能是与一个无误的形式相关联的。事实上,他们坚称,最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包括早期的改教家,充分认识到圣经在保持忠实履行其功能的同时,在形式上是有错误的。他们坚称早期的改教家(以及约翰·欧文之前的英国清教徒)通过关注圣经的功能,确立基督为中心,并保持了其神学的实践性。改教家们保留了奥古斯丁的观点,即一个人必须相信才能理解。他们得出这一认知是认识到神自己俯就人类——神的话语是以人的语言来具体体现的。罗杰斯和麦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误差是不可避免的,但丝毫不能减损圣经的救赎功能。
根据罗杰斯和麦金的观点,关注形式的无误是对改教家观点的严重背离,这种关注反映了对圣经功能关注的失落。尤其是这意味着丧失了以基督为中心,高举抽象的神学,不能理解在圣经中神俯就的作为,并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认为人必须理解才能相信。
本文将依据五个关键领域的证据,展现罗杰斯-麦金论点的不适当之处:(1)路德的思想;(2)加尔文的思想;(3)改革宗的信条和要理问答;(4)英国清教徒传统;(5)欧洲大陆改革宗正统。
路德
路德(1483-1546)是一位最英勇和迷人的历史人物。他改教信息的传播与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萨克森教区的讲坛和维腾堡课堂,他的思想不断吸引和刺激他的学生。毫无疑问,他的神学是深刻地以基督为中心的,他强调圣经的信息是基督。正如路德所说:“基督徒接受基督——神的儿子——作为圣经的中心内容。学习并了解了他,其余的就都变成有意义的,所有的经文都变得清晰易懂。”[6]因此路德无可质疑地强调圣经的救赎功能。
然而,对于罗杰斯-麦金和其他人所说的圣经功能和圣经形式的二分法,路德并不接受。路德关注有关圣经形式的问题,他对圣经形式的观点是明确的:圣经是无误的。路德下面的话显明他对形式无误的看法:“但是,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教父们)作为人都会有出错的时候,因此,只有当他们以从来不会出错的圣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我才会相信他们。”[7]而且,“神的道是完美的、宝贵的、纯洁的,它是真理本身。在它里面没有虚假。”[8]他对形式的关心也具体地表达出来:“不仅字句,圣经和圣灵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也是神圣的。”[9]路德还说,“一个字母,甚至经文的一点一划,对我们的意义都超过天地。因此,我们甚至不能允许最微小的改动。”[10]
就是在路德最著名的名言里,也印证他对圣经形式的关注。1521年,在查理五世皇帝和世界权力的面前,路德出庭沃木斯议会,他指出圣经作为宗教权威,是构成他所宣扬的福音的基础。他说:“除非我被圣经或明白的理由说服,否则我不会单单相信教皇和会议,因为已经证实他们往往有错误和矛盾。我所引用的话语已经征服了我,我的良心被神的话语俘虏,我不能、也不会放弃任何东西,因为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既不安全也不诚实。”[11]这句话的内涵就是路德的信念——神的话语俘虏了他,这话语并不自相矛盾,也不会出错。
路德在他的神学里也使用了他对圣经形式绝对可靠的确信。特别是在捍卫他的圣餐神学时,路德展示了他对圣经的精确词语的信任。在回答慈运理(Zwinglians)时他强调了圣经的话语形式以及功能:
所以,你可以在你死亡或在最后的审判中,快乐地对基督说:我亲爱的主,对你最后晚餐的话语,我们发生了争论。有些人希望它们被理解为与它们所说的不同。然而,因为他们不能指教我任何东西,只会使我陷入混乱和不确定……我一直以你的文本作为文字标准。如果其中有费解的,如果我不完全理解它们,你会容忍我,就像你当年忍耐你的使徒。例如,在你向他们讲论你的受苦和复活时,他们有许多事情不明白,但他们保留你的话并没有改变它们。对于你亲爱的妈妈,当你告诉她,“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2:49)她也不明白,但她把这些话藏在她心里,并没有改变它们。这样,我也保存你的这些话语:“这是(is)我的身体”,等等。看哪,没有哪个宗教狂敢如此与基督说话。[12]
路德很愿意把他的一个主要神学问题建立在这个小词汇(is)形式的精确上,因为他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
罗杰斯和麦金分析路德神学,认为那些伟大的改教家不关心圣经的形式,这与路德自己的证词正相反。他们指出路德强调在圣经中,神自己俯就对人说话。圣经俯就人是以一种类似于永恒的话语(道)成为肉身的方式。对于罗杰斯和麦金,俯就意味着圣经是用“脆弱和不完美的人的话”写的。[13]他们引用路德的话说,“圣经没有外部的荣耀,也没有吸引任何注意力,缺乏美感和装饰。”[14]
然而,罗杰斯和麦金在他们的书中严重误用了路德和其他人的“俯就”概念。他们没有真正的考查,就假设塞内加(Seneca)的格言是绝对真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神在圣经里俯就人类的语言,那么,他们就假设它必定包含错误。但是,在所有人类的事情中,错误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吗?俯就原理与道成肉身是同一类的,这就是问题的焦点。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形式是与他的拯救功能无关的吗?耶稣作为人(他的形式)不是他的工作(他的功能)的基础吗?基督耶稣作为人所说的话不是无误的吗?路德所使用的俯就原则非但没有与圣经无误冲突,事实上正好相反。
路德对圣经缺乏美感的评论也与圣经无误的教义一致。这是路德在文艺复兴时期针对古代文学作品复苏的背景而写的。路德跟别人一样注意到,相比西塞罗(Ciceronian)的修辞,圣经是平凡和缺乏美感的。但路德并不认为圣经的朴素简单减损了耶稣基督启示的清晰、效力或权威。路德承认圣经没有用这个世界的雄辩口才说话,但并非承认圣经有误,缺乏文体的宏伟不是一个错误。
此外,罗杰斯和麦金还提到所谓的路德承认圣经在细节上错误的具体实例。他们的错误列表是取自瑟伯尔(Reinhold Seeberg)的《教义历史》一书对此课题的一页纸的讨论。[15]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没有认真对待与他们持不同观点的几份重要的二手材料。[16]例如,保罗·阿尔托依兹 (Paul Althaus)非常受人尊敬的作品《马丁·路德的神学》对路德观点的总结:“圣经从不出错。因此,它本身就有绝对的权威。”[17]伍德(A. Skevington Wood)在《话语的俘虏——马丁路德:圣经博士》中得出结论:“路德的默示教义是与无误教义密不可分的。”[18]拉吴(M. Reu)在他的《路德和圣经》这项非常认真的研究中得出同样的结论。[19]
那些试图否认路德认为圣经无误的人,也使用其他论据。他们常常指出路德对某些书卷的正典性有疑问。但这些论据是不相关的,合乎正典和无误是完全不同的神学主题。然而,路德对正典的疑问也表明他对圣经形式的关注,这确实表明他将形式和功能(正典和福音信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有时,路德承认福音书之间存在调和的问题,也被引用为他拒绝圣经无误的证据。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耶稣洁净圣殿,在马太福音里,这记载在耶稣传道事工的后期,而在约翰福音里却是在事奉开始不久。[20]一些学者引用路德的话:未能调和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之间的这个差异,并不能破坏一个人对基督的信仰。[21]但是在上下文中,路德的说法并没有表明圣经的形式有不一致或圣经中存在错误。路德在此实例中首先提出了各种调和的可能性。他也给出他自己对这些解答的首选。然而,他并没有坚持自己的解决方案,他承认,“这些问题存在,并将继续存在。我不会斗胆去解决它们,也不必要。”[22]他解释说,这样的问题存在,部分原因是福音书的作者并不一定想要给出时间次序,并且基督教信仰并不需要充分了解所有的时间细节,“福音书的作者们都同意这一点,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但在他们的记载中,他们并不遵守一个统一的次序,而往往忽略原本的时间次序”[23],但缺乏时间顺序不是一个错误,路德在处理另一个调和的问题时说:“路加在他的福音书一开始就说,他想要按照次序从头记录所有的事情……所以,马太没有按照确切的次序记载,但路加这样约束自己,并确实这样做了,这并没有问题。”[24]很清楚,在面对某些经文的调和问题,并承认福音书作者不同的方法时,路德的确关注经文的形式,但并没有把这些归结于圣经的错误。
对路德的圣经权威观的简短研究做个总结:人们必须记住,路德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研究的影响。他承认风格的差异,并在圣经研究中对背景很敏感。他用最好的学术工具去研究圣经。但他致力于学术研究并非基于功能和形式的分离,不是罗杰斯和麦金所说的:“因此,路德的信心在于圣经的主题,而不是它的形式,形式是学术研究的对象。”[25]路德拒绝任何这样的二分法。理性和学术是理解圣经的有用工具,但必须以真实信心来使用,并且必须最终服在圣经的形式和功能之下:“相信和阅读圣经意味着我们从基督的口中听话语。当你听见的时候,你知道,这不只是人的话,而真正是神的话。”[26]
加尔文
加尔文(1564-1509)是第二代改教家中最辉煌的一位。他的背景与马丁·路德非常不同。他是在法国北部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他在古典文学和法律方面受到了良好的人文教育。他不像路德那样深受经院神学的影响。他一生的工作大部分是在瑞士城邦完成。路德的写作多是关于特定的神学主题或详细和扩展的注释,而加尔文则是一个系统神学家(例如他的《基督教要义》),并以他“清晰简洁”的风格写了许多圣经书卷的注释书。
尽管有着这样不同的个人历史,加尔文认为他自己的神学与路德的非常相似。虽然有不同,特别是在圣餐方面,但加尔文视自己为路德开创的神学运动的一部分。在圣经权威方面他们的神学确实一致,加尔文和路德一样,强调圣经的拯救功能的首要重要性:“总之这是我们要寻求的:真正认识基督,以及在他里面、由他从父神那里提供给我们的无限财富。”[27]
加尔文和路德一样,在他的圣经论中并没有将功能和形式分割。形式以及功能都是来自神自己,正如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的名言:“唯有当信徒深信圣经是来自天上的启示时,圣经在信徒心中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就像他们在天上听到神活泼的话语一般。”[28]他会说使徒“是圣灵真实和无谬的文士,且我们应当将他们的作品视为神的圣言。”[29]在另一个明确的陈述中,加尔文将信仰的确据和圣经拯救的信息与经文形式的绝对真实性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们把信心看作是:对神旨意的认识,是从他真道中获得的。因而,这信心的根基乃是要先确信神的道是真理。只要人心里仍怀疑神的道是真理,他必定会质疑这道的权威,或根本不相信这道。事实上,就算相信神是信实的、不能说谎的,也仍旧不够,除非同时毫无疑惑地确信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都是圣洁和不可违背的真理。[30]
在他的注释书中,加尔文也证实他相信圣经文字的真实,表明他对圣经形式无误的信心。在谈到诗篇119:105对律法的赞美时,加尔文说:“因此,让我们确信,在那里可以发现那无误的光,已经提供给我们,只要我们张开眼睛去看它。”[31]在对提摩太后书3:16的注释中,加尔文在谈到圣经的权威和益处时,既区分圣经的形式和功能,也将两者结合在一起:
首先,他(保罗)因圣经的权威而赞美,然后又因为来自它的益处而赞美。为坚持圣经的权柄,他教导我们圣经是神的默示,因为,如果是这样,人毋庸置疑应该敬畏地领受它……这是第一层意思,我们对待圣经应该有对待神一样的敬畏,因为圣经唯独来源于神,没有任何人类的来源混入其中。[32]
他对圣经形式的绝对信任,表现在他对圣经的细节的依赖上。在注意到彼得前后书的风格差异,并承认一些古代教会否认彼得后书的正典性之后,加尔文总结:“如果它(彼得后书)被接受为正典,我们就必须承认彼得是作者,因为他的名字写在经文里,他也证实他与基督一起生活过:若将它归于另一个作者,就是一个虚假的、不配的基督仆人。”[33]其实,加尔文断定那些认为神话语有误的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
他肯定了他对神的话语的爱不是冲动或盲目轻率的感情,而是因为它好像炼过的金子或银子,纯净没有一点渣滓……几乎没有人是没有犯玷污神话语的罪——要么由于他们的不信,或任性,或骄傲,或奢侈淫逸!肉体是如此地叛逆,将所启示的真理与炼尽的精金相比,以至于它(真理)在所有污秽中闪耀出纯洁的光辉,这是个极大的称颂。[34]
与上面引用的这些证据相反,罗杰斯和麦金,还有另一些人试图表明加尔文不接受圣经无误。他们的做法是呈列他们认为加尔文没有坚持无误的各种证据。其中一些材料类似于上面关于路德的引用。他们注意到,加尔文看见神在圣经中对人的俯就,他们就不加论证地假设,加尔文认为圣经是用“不完美的语言”写的。[35]跟前面提到路德时一样,俯就原则并不意味着存在错误。
罗杰斯和麦金先生也注意到,加尔文承认圣经并不总是以高贵的风格写作的,[36]但他们错误地推断这表明加尔文缺乏对圣经形式的关注。加尔文跟路德一样,提到圣经风格的朴素,并不是指责它错误,而是针对西塞罗派人文主义的批评为圣经做辩护。
在跟路德相同的讨论之外,罗杰斯和麦金也提出了新的论据和证据。他们指出,加尔文认为新约对旧约的一些引用是转述而不是精确的引用。他们推断,加尔文视这些为“不完美”和“不准确”。[37]但加尔文并没有这样说,转述并非自证其错误。事实上,加尔文认为转述是合法的,恰恰表明使徒写作所采用的形式正确,并保护他们免受错误的指责。同样,加尔文指出新约中对旧约的一些经文的使用并非完整的解释而是一些联想和应用,罗杰斯和麦金认为加尔文辨认出一些错误。但在罗杰斯和麦金先生引用加尔文的原话里,加尔文说他做了这样的观察是之后显示使徒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妥”[38]。加尔文不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罗杰斯和麦金说,加尔文还认识到另一种科学领域的错误。他们指的是加尔文说摩西写创世记不是作为一个科学家,而是作为一个神学家。[39]加尔文认为神学家以通俗的语言谈论科学问题——以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例如,“太阳升起”)而不是科学准确的语言——是正当的。加尔文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并没有错误地陈述真相。加尔文并没有接受一种二分法,即将“科学”真理放在圣经启示真理的对立面。根据加尔文,神学家和科学家讨论自然现象的词汇、目的、角度和全面程度都会有所不同,但都是教导同样的真理。在这方面,同样没有证据表明加尔文认为圣经中有错误。
罗杰斯和麦金还提出了一些似乎是决定性的证据:加尔文在对使徒行传7:16的注释中宣称,路加“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40]然而,在这个例子中,错误的是罗杰斯和麦金。加尔文实际上说:“但当他(路加)继续说,他们被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抹子孙买来的坟墓里,这里亚伯拉罕的名字很明显是一个错误,必须进行相应的修改。”[41]加尔文确实认为在使徒行传7:16有一个错误,还坚持修改文本。但他没有明确地把错误归因于路加。事实上,在上下文中,加尔文很可能所指不同。在两个段落之前,加尔文在注释使徒行传7:14写到:
司提反说雅各带着七十五人来到埃及,与摩西记载的只有七十不同,……所以我的结论是,这个不相符来自于抄写误差(希腊文抄本)。但是,这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路加不想让习惯于阅读希腊文的外邦人在这件事上被搞糊涂。他自己也可能写的是正确的数字,但有人错误地把摩西的经节改动了……若有人坚持争论这一点,我们就让他拥有高高在上的智慧吧。让我们记住,保罗禁止我们对家谱好奇和纷争(多3:9)不是没有道理的。[42]
从这些问题引出了几个要点。首先,加尔文不认为一个人应该过分地被经文的调和一致问题所困扰。徒然的好奇对属灵生命是一种危险。第二,在认识到他在调和文本遇到的问题时,他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路加在他的写作中犯了错误。加尔文并非对文本的形式漠不关心,而是在使徒行传7:14上花了很多笔墨来研究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文本的形式。第三,他自己对7:14的答案是,抄写员犯的一个错误,这是最有可能的。因此,他假定使徒行传7:16的误差来自相同的起源,事实上他对使徒行传7:16文本应该修改的坚持,几乎肯定意味着他认为这是一个抄写错误。罗杰斯和麦金想从这样的证据得出加尔文承认文本的“历史性错误”[43]的结论,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44]
总结如上对加尔文圣经权威性的简短的研究,反思一下约翰·利思(John Leith)令人兴奋的观察是有帮助的:“学者对加尔文是否相信字句无误意见不一。证据似乎指向一个比今天所理解的字句无误更自由的理解,虽然加尔文确实坚持圣经是神的话。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因为加尔文从来没有以任何接触批判性历史研究的人一定会提问的方式面对过这个问题……为此,在加尔文那里去找现代历史意识提出的新问题的答案,是徒劳的……”。[45]利思坚持认为加尔文没有面对过现代的圣经批判是对的。关于一些现代相信无误的人偶尔会对加尔文对经文的调和方法有困惑,他也可能是对的。[46]当然不能期待加尔文会预料到现代圣经批判者提出的所有具体问题。但当“现代历史意识”部分或全部否定圣经为神的话语时,当它站在圣经是否完全真实与可靠的审判地位时,加尔文的立场是明确和有价值的——圣经就是神的道。加尔文会坚持现代的基督徒和第十六世纪的基督徒一样,必须把所有思想都服在神的道之下,让圣经作为人的真理判断标准,甚至是人的历史意识的判断标准。加尔文致力于最好的学术研究,但拒绝圣经的救赎功用和圣经形式之间的二分法:圣经的救赎功用是牧者们关注的,而圣经的形式是各自为政的学者们关注的。[47]加尔文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它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我们发现加尔文显然是相信圣经无误的。
改革宗信条和要理问答
改革宗信条和要理问答强调圣经的救赎信息,那是改革宗与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区别点。改教家们认为,圣经包含了完整和清晰的救赎信息,基督徒不需要添加传统或教会的权威性解释。改教家与罗马天主教在整本圣经的真实性上没有任何争议,因此,为圣经的可靠性辩护在信条和要理问答里并不显著。然而信条确实致力于坚持圣经的完全真实性。有几个例子足以表明这些信条对圣经无误的委身。
加尔文的《日内瓦要理问答》(1545)宣称圣经的一个益处:“我们全心相信它就是从天上赐下来的真理。”[48]在加尔文的帮助下写成的1559年的《法兰西信条》,宣称神的话是“真理的法则”。[49]《比利时信条》(1561)对这点的陈述更全面,它宣称圣经“无可指摘”[50],是“无谬真理”[51],基督徒“完全相信且毫不怀疑其中所写的一切”。[52]
《海德堡要理问答》也在其关于信仰的定义(第21问)中宣称:“我把握到神在他的话语里向我们启示的一切真理。”撒迦利亚·乌西努斯(Zacharias Ursinus)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作者之一,他在注释这一说法时,写道:信仰的一个基本要素“是顺服赞同神赐给教会话语的每一个字”[53]。他坚持忠实的基督徒“相信圣经包含的每一件事是真的,是从神来的”[54]。
英国清教
英国清教徒因其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其在美国教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吸引了众多的解释者。由于其发展的独特环境,清教徒主义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神学运动。清教徒主义是从教义已经归正,但(在清教徒看来)实践没有充分归正的英格兰教会里发展起来。结果就是,清教徒的神学兴趣往往集中在教会和个人实践,有一种特殊的实践性。
罗杰斯和麦金对清教徒神学的独特性的强调成为其论点的基础,他们认为英国清教是十七世纪改革宗神学经院哲学的早期成就的一个例外。他们认为,实用而非学术的清教徒神学,来自独特的教会体制和英国的哲学取向,[55]使得清教得以免除过度关注圣经形式和无误教义。
然而,清教徒神学与它独特环境的相互作用,实际上并没有为罗杰斯和麦金的进路提供根据。[56]清教徒和欧陆的改革宗神学家皆认为自己是国际改革宗联合群体的一员。例如,英国彻底地参与多特会议;[57]清教徒,如威廉·艾莫斯(William Ames),高举多特的神学论述。英国清教徒和欧陆改革宗神学家几乎所有的神学观点都一致,包括圣经无误的信念。
罗杰斯和麦金争辩说,英国独特的哲学环境甚至比其独特的教会体制更重要。在英国清教徒里彼得·拉米斯(Pete Ramus)的哲学占主导地位。这种哲学方法更多保留了奥古斯丁的修辞传统,并声称拒绝亚里士多德。罗杰斯和麦金认为是拉米斯使英国清教保持关注圣经信息,而没有落入关注圣经形式无误。
然而,拉米斯主义并不具备罗杰斯和麦金所声称的神学决定性。拉米斯主义方法论往往被亚里士多德方法论的神学结论所取代。例如,拉米斯主义者阿米念严厉抨击拉米斯主义者帕金斯(Perkins),因后者持坚定的堕落前预定论的观点,而亚里士多德派的霍马勒斯(Gomarus)则为帕金斯辩护。拉米斯主义并不一定像罗杰斯和麦金所说的在理性上保持一致。例如,莫伊斯·阿米若特(Moise Amyraut)受到拉米斯主义传统的很大影响,[58]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阿米若特是理性主义者,是在于他将所有真理放在理性的检验之下。”[59]
威廉·艾莫斯(William Ames)是最强有力的例证,证明罗杰斯和麦金要表明清教徒不接受圣经无误的努力是不恰当的。艾莫斯是一个抗争的清教徒(不信奉英国国教的),又是拉米斯主义者。他写了一本最具影响力的清教徒神学手册:《神学的精髓》(第三版,1629)。然而在这本书中,与人们根据罗杰斯和麦金所期望的相反,艾莫斯清楚地教导圣经无误。关于圣经作者受到默示的方式,艾莫斯说:
有些事情透过自然知识而得知,有些透过超自然而得知。在那些被隐藏和未知的事物中,神的默示单独工作。在那些已知的事情或是通过普通手段获得的知识中,作者的虔诚热情被加增(神帮助他们)以致他们的写作不会有误。
无论是关乎正确还是事实,在所有由超自然启示而得知的事情中,神不仅默示他们要写的主题,而且授意他们应该的遣词用字。但这是通过一个微妙方式实现,让每一位作者都会以最适合他的个性与背景的方式来写作。[60]
这说明,艾莫斯确实关心圣经的形式,他确实明确宣称圣经的无误。
改革宗正统
正如在这项研究的引言中所指出的,改革宗正统一直是相当重要的学术研究和辩论对象。要在早期改教和正统时期之间更精确划分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将需要许多更深入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必须注意十七世纪的正统神学家所面临的新的历史形势。正统神学的详细情况不能只是抽象地研究。不考虑产生十七世纪正统的历史背景,也不足以完全确定它的结构。
罗杰斯和麦金以他们关于改革宗正统[61]的一章进入这个学术讨论。这一章的第一部分考察了改革宗正统的不同发展阶段,第二部分分析了弗兰西斯·图伦丁(Francis Turretin),改革宗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罗杰斯和麦金坚持,正统的发展是对改革宗以基督、信心和圣经的救赎信息为中心的教导的一种持续稳定的侵蚀。他们认为,正统代表了在圣经形式上逐渐超过圣经的救赎功能。他们认为,圣经无误的教义是在这个衰落的时代里在更正教中兴起的。
在本次简要的研究中,不可能考察罗杰斯和麦金在这方面的所有主张。[62]然而,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正统仍然关心圣经拯救信息的中心地位,同样,早期改教家一直在关注圣经形式无误。正统在讨论圣经形式的权威方面,保持了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早期改教家的重点,这点也应该是清楚的。在本文中我将以一个简短的对方法论的观察来讨论正统,然后对弗兰西斯·图伦丁的工作做更深入的分析。
从方法论上来说,罗杰斯和麦金一开始正确地认识到十六世纪晚期,索西奴派(Socinianism)的崛起和罗马天主教的复兴对更正教构成了重要的威胁,[63]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威胁的严重性。他们似乎很快忘记了这些改教的继承人必须回应神学发展的新挑战,而这些新挑战往往是在圣经形式的权威方面:索西奴派坚持理性的决定性作用,天主教强调提炼过的罗伯特·贝拉尔米诺(Robert Bellarmine)和其他人关于教会权威的论点。正统的更正教必定要更精炼地予以回应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圣经完全可靠,是唯一的权威。但是,在他们对圣经形式的合理的、学术性的关注里,正统只是继续早期改教家所开始的工作。证据也表明,正统也继续坚持福音救赎消息的重要性。[64]
图伦丁(Francis Turretin, 1623-1687)出生于日内瓦一个意大利的改革宗家庭。他的父亲是牧师和神学教授,他在日内瓦接受正统神学教育,自己也成为一位牧师以及日内瓦的神学教授(1653-1687)。他最著名的著作就是《系统神学》(Institutio Theologiae Elencticae)。
对于罗杰斯和麦金来说, 图伦丁是改革宗经院哲学对圣经形式无误的兴趣已经消亡的缩影。他们认为:“图伦丁意识到加尔文对圣经的看法与他自己的观点对立”。[65]他们特别关注图伦丁对圣灵和理性在证明圣经权威上的作用的理解。他们也批判他对圣经研究的学术进路,以及俯就的概念在他的圣经观里所扮演的角色。尽管本文不能对图伦丁所持有的历史影响力作全面研究,也不能对图伦丁圣经观作全面研究,但它可以显明罗杰斯和麦金的方法存在着严重的不足。[66]
罗杰斯和麦金批判图伦丁没有将圣经信息——它的救赎功能——的权柄建立在圣灵的内证上。他们认为图伦丁将圣灵的工作范围限制在相信圣经形式无误这件事上。[67]但是图伦丁强调圣灵的作用:
神透过圣灵(供应者)教导信徒(耶31:34;约1:43;约一2:27),并不会让圣经变得比较不必要;因为赐下圣灵不是为了给我们新的启示,而是将写成文的话语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话语不能与圣灵分离(赛59:21)。前者做客观的工作,后者做有效性的工作;前者冲击关闭的耳朵,后者打开内心。圣灵是老师,圣经是他教导我们的教义。[68]
图伦丁所说的圣经教义或信息,不是一些形式上的问题,而是圣经的内容,他在其他地方总结这些为:
美好崇高的奥秘,是即便没有什么敏锐理性的洞察就能够发现的,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基督的偿还、死人复活等等。例律的圣洁与纯净,可以校准思想和影响内心,并使人在每一种美德上完全,与他的创造主相配……[69]
与罗杰斯和麦金相反[70],同样清楚的是,图伦丁并非从圣经形式的无误导出圣经的权威。他确实认为若圣经有错误就不会有权威,并花了大量工作来证明圣经无误。但他很清楚,圣经的形式无误是由于它的神圣权威和起源:“我们刚才讨论的,圣经的起源决定了它的权威,只是因为它是从神来的,就必会是真实的和神圣的。”此外,“当圣经的神圣性被证实的时候,也必然得出其无误性。”[71]
图伦丁还较为详细地探讨了人如何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他清楚地说,只有圣灵才能使一个人相信圣经的神圣源头。与加尔文一样,图伦丁认为是圣灵令人信服,不是透过教会的见证,而是透过圣经本身:“但圣灵用来让我们相信真理的论据或最根本动力”,不是“自然的、天主教说的教会的见证,”而是“人为的、我们所持守的、源自圣经本身的标记”。[72]图伦丁进一步声称:不仅圣经对其自身的宣称(其自证性)建立其权威,而且圣经的标记也建立其权威:
圣经,当它宣称它是神的启示,不仅权威地证明自己的神圣,也以一种天然论据或见证的方式证明自己的神圣,虽然这个宣称本身对那些认信的基督徒很有用,却不能用来对付那些拒绝它的人。但根据人为论据的推理,即从神赋予圣经的标记,却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因为作为神的作品,在我们的眼中,显然一定具有设计者自己无与伦比的卓越,就好像太阳自己的光使自己被看见;所以他希望在圣经里,这从众光之父和公义的太阳发出的光彩,散发出各种神圣的光芒,会让自己被人知晓。[73]
在图伦丁讨论圣经标记时,他区分外部和内部的标记,其中内部标记更有说服力。[74]外部标记包括圣经的古迹和保存,写作这作品的作者的软弱,以及殉道者和众人的见证。[75]内部标记是圣经的主题(基督和福音)、风格、形式(教义的一致)和目的(神的荣耀和人的救赎)。[76]
对通过圣经的标记证明圣经的各种可能性,图伦丁的讨论完全与加尔文一致。加尔文说:“真的,如果我们想继续争论,许多事情我们可能会很容易证明——如果有神在天——律法、先知与福音是从神而来的。”[77]加尔文甚至列出了这样的证据:“当我们通过热切的研究,思考神智慧的精细,如此有序的布置;其教义完全神圣的属天特征,没有一丝尘世的味道;各个部分彼此美丽和谐,以及其他使其作品庄严的品质,给了我们多么美妙的明证。”[78]加尔文还讨论了其他的确据,如圣经古迹,伴随着启示的神迹,并整个教会和殉道者的见证。[79]加尔文所列出的证据与图伦丁所列的标记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加尔文和图伦丁在这些标记的用途上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加尔文坚持认为,人相信圣经不依赖标记或证明。他热情地宣称:
因为,即使它[圣经]因它自己的威严而赢得了尊敬,也只有当圣灵把它印在我们的心里,它才会真正地影响我们。因此,在他大能的光照下,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或别人的判断;但在所有人类的判断之上,我们完全肯定(就像我们看到神自己的威严一样)它是出于神的口,透过人的事奉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判断不依靠证据,不依靠标记的真实性;而是将我们的判断和智慧服在它之下,远远超出服从只是猜想出来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不是像习惯于抓住一些未知的事情的人,密切审视它们,而是完全意识到我们拥有无懈可击的真理!……我们感受他神圣威严的生命和呼吸的无可质疑的力量。这种力量吸引并点燃我们,有意识地并心甘情愿地服从它,但比单纯的认识或意愿更充满活力和有效。[80]
虽然加尔文并不是在谈论一些非理性的神秘主义,但他确实认为接受圣经的权威比认识圣经的权威更深刻:这是富有情感的。他似乎是在谈论对圣经真理的直觉:“他们的问题——除非我们倚靠教会的法令,否则我们如何才能确认这是从神所发出的呢?——就好像有人问:我们从哪里学会分辨黑暗和光明,黑色和白色,苦和甜呢?”[81]对于加尔文来说,证据是“非常有用的辅助,”[82]但只对那些已经接受圣经的人有用。
图伦丁在某种程度上超出加尔文,主张标记或证据对于接受圣经可以(但不必须)是有用的。他坚持:
虽然信仰可以建立在见证的权威上,而不是科学论证上,但不见得不能有人为论据的辅助,特别是在建立信心的原则上:因为在信仰可以相信之前,它必须有神圣的见证人,他的信仰是被给予的,除非某些真实的标记明确地建立,否则就不能相信。因为,对任何人来说,缺少合适的相信的理由,这样一个证人的证词是不值得相信的。[83]
图伦丁说,信仰在可以相信之前必须有内容可以相信,这跟加尔文一样,但进一步,图伦丁认为,理性的论证可以用来支持所需要相信的,这跟加尔文不一样。
虽然加尔文和图伦丁之间在这点上有差异,但这一差异与无误的主题并不直接相关。加尔文和图伦丁同意无误的教义,差异只在对圣经权威的证明是否在使人相信圣经上有用。这种不一致可能标志着,理性和亚里士多德对图伦丁比对加尔文起到更大的作用,但不代表是罗杰斯和麦金所认为的对一些基本改教观点的背叛。[84]
进一步,图伦丁的正统没有使他远离早期宗教改革发展的人文释经原则。他没有为了系统神学家的方便而将圣经简单罗列为一系列命题或文本证据。[85]他坚持严肃地对待任何圣经文本的语境:
要确定圣经的真正意义,释经是必要的,不仅对版本中所含的词汇,也对事情……但对于释经而言,在对神热诚的祷告后,还需要探究来源,了解语言,区分特殊词汇和形象词汇,注意范围和情境、整体段落和前后联系,消除成见,并用信心推理对解释的确认。[86]
他还充分认识到圣经作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选择并安排素材:“因为这些历史并非为每一个情境所包含的细节而记载;无疑有一个狭窄的范围,很多东西被包含进来,其他的东西似乎没有那么重要,就被省略掉了。”[87]
在处理圣经表面的错误上,图伦丁也接受自己的观点之外其他学术观点的合法性。在这个方面,他肯定没有将信心只放在一个理论上。[88]他教导说:
也有人认为,一些很细微的错误已经悄悄进入圣经,即使现在也还存在,它不能靠任何收集文稿而改正,然而,这不可归咎神圣作者本身,而部分是时间带来的损耗,部分是抄写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错……因此斯卡利杰(Scaliger)、卡佩利(Cappellus)、 艾马慕斯(Amamus)、福修斯(Vossius)等人这样认为。最后,另一些人捍卫圣经的完整性,说这些各种矛盾只是表面的。[89]
图伦丁持有后者的意见,为它力争,但仍认前者为正统。
在相关领域,许多人批评图伦丁在《瑞士联合信条》(Formula Consensus Helvetica,1675)的预备及其传播所起的突出作用。他们指出,特别是对信条中的这些话:“但是,特别是旧约的希伯来原文,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仍然保留着犹太会堂所传承下来的原文,……不仅在于它的子音,而也在于母音——无论是指向母音自己,或至少是这些指向的能力;不仅在于事情本身,而也在于它的话语,都是神默示的……”[90]他们声称这些话显出知识的荒谬,而无误的支持从这里而出。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两点观察。首先,在图伦丁的时代,《瑞士联合信条》的立场不是荒谬的,而是一个站得住脚的学术理论。[91]图伦丁和其他《瑞士联合信条》支持者重申了自己的信念,既根据子音也根据母音的重音,他们拥有圣经的真实文本。他们继续人文主义式地强调原始来源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他们拥有希伯来原文文本的一个可靠的副本,并拒绝为翻译的缘故修改该文本。[92]他们认为马索拉文本的母音指向忠实的原文再现,因此拒绝对此发声法的批评。
第二个观察是,现代的学术研究已经表明,在关于文本的问题上,《瑞士联合信条》的立场是错误的。图伦丁认为他拥有一个完全可靠的希伯来原文副本,这并不成立。但现时代对图伦丁的希伯来文本观的拒绝,并不表明他对圣经权威的委身是荒谬的。图伦丁确实把他对希伯来文本的看法作为他辩护圣经无误的权威之一个元素。他认为,基督徒拥有无误原文的无误副本。但他的辩护的一个元素的崩溃,并不会让原文无误的教义站不住脚,无论是对图伦丁或是对那些继续跟他持有同样观点的人。
罗杰斯和麦金认为,图伦丁的圣经权威观的形成的高潮在于他放弃俯就的概念。他们宣称,“图伦丁完全没有”俯就的概念。[93]但再次,这里误解了图伦丁。他清楚地说:“当神知道,他知道自己,因他是无限的,所以他的知道也是无限的;但是当他说话时,他不是在对自己说,而是对我们说,即,俯就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许多方面不能领受。”[94]他也以其他方式承认这原则:“神被称为亘古常在者(the Ancient of Days…Days),因此,年日的说法对他来说并不恰当,而是照着人的方式来说的,因为我们活在时间中,若不跟我们所处的时间关联我们什么都不能理解。”[95]“‘后悔’是把对人说话的神方式用在神身上,但必须按照神的方式来理解。”[96]
罗杰斯和麦金总体上批评更正教经院哲学,认为它因为对抽象思辨神学的过分关注吞噬了神学的实践性关注:“精密取代敬虔成为神学的目标。”[97]再次,这样的描述并不适合图伦丁。图伦丁定义神学为部分理论和部分实践的混合学科,并认为“实践超过理论。”[98]他坚持神学的理论要素(他定义为知识,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问题)以反对索西奴派和抗辩派。他认为,纯粹的实用神学是道德主义。他警告说:“索西奴派和抗辩派……说神学是如此完全实际的,其中没有什么对救恩是必须的,除非涉及到道德律令和承诺……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抹杀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教义知识的必要性。”[99]但他致力于理论和实践混合的神学并没有使他远离敬虔。而是有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生气勃勃的神学异象,正如下面的陈述所表明的那样:
这种神学是混合的,也就是说,部分理论和部分实践,可以给出以下证明。1.对象,认识和敬拜神作为首要真理和最高的善。2.主体,在对真理的认识中人可以被完善,透过真理他的理解可以被光照,喜爱良善,透过真理他的意愿可以被装饰,信心变为可靠,在爱中实践。3.原理,外在和内在,外在:神的话语,包括律法和福音,前者阐明应该做的事情,而后者是所要知道和相信的,因此称为敬虔的奥秘和生命的道;内在:圣灵,就是真理和成圣的灵,以及知识和敬畏主的灵。[100]
上述对图伦丁的讨论并未有定论。在他的思想中,无疑有其他这里没有提出的因素代表他与早期的改教家们不同。然而,明确的是,在圣经论的根基上,加尔文和图伦丁引人注目地一致:两人都强调圣灵在建立圣经权威上的工作,两人都相信圣经的威严和神圣是可以证明的,两人都承认圣经的历史性和俯就性,两人都视圣经的信息具有中心性,加尔文和图伦丁都不担心圣经的形式会破坏福音信息,两人都教导圣经无误。
结论
释经与神学构成了圣经无误之争的中心阵线。该中心的强度最终会决定对圣经的本质之争的结果。然而,在这场冲突中,关于教会对圣经态度的历史成为一个重要的侧翼阵线。坚持无误的人为了是否可以合法地将教会历史作为他们的盟友,已经发生过各种小规模冲突。但愿本文对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研究所代表的尝试可以将讨论推进,并帮助重新确认圣经无误是历史性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元素。
罗伯特·戈弗雷(W. Robert Godfrey)博士从1981年起,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加州分校教授教会历史。此前他曾在哥顿·康威尔神学院、斯坦福大学和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任教。他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加州校区的第三任校长,北美联合改革宗教会(United Reformed Churches)的牧师。曾在许多会议上发表演讲,包括由世界福音派大会洛桑委员会、费城改革宗神学大会、Ligonier事工机构等举办的会议。
[1] 本文取自:http://www.difa3iat.com/8947.html/(2016年4月5日存取)。原文:W. Robert Godfrey, “Biblical Authorit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A Question of Transition,” in Scripture and Truth, edited by D. A. Carson and John D. Woodbridg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a division of Baker Publishing Group), 1992, pp.221-243. 承蒙版权方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 ——编者注
[2] 参,例如,Richard Lovelace, “Inerrancy: 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Inerrancy and Common Sense, ed. Roger R. Nicole and J. Ramsey Michae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0, pp.21-25; Geoffrey W. Bromiley, 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8, pp.327-28; Edward A. Dowey, Jr., The Knowledge of God in Calvin’s The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99ff.; 也可参考Robert Preus和John Robinson两位作者的研究。
[3] 参, 例如, John Warwick Montgomery, “Lessons from Luther on the Inerrancy of Holy Writ,” in God’s Inerrant Word, ed. John Warwick Montgomery, Minneapolis: Bethany, 1974, p.69。
[4] 参, 例如,Jill Raitt, The Eucharistic Theology of Theodore Beza, Chambersburg: Pa.,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1972; John S. Bray, Theodore Beza’s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Nieuwkoop: De Graff, 1975; W. Robert Godfrey, “Tensions Within International Calvinism: The Debate on the Atonement at the Synod of Dort, 1618-1619,”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4。
[5] Jack B. Rogers and Donald K. McKim, The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An Historical Approach,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79.
[6]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ed. J. F. K. Knaake et al. (Weimar, 1883–) (hereafter cited as WA), vol. 44, p.510, cited by Willem Jan Kooiman, Luther and the Bible, Philadelphia: Muhlenberg, 1961, pp.235-36.
[7] Luther’s Works, edited by Jaroslav J. Pelikan and Helmut T. Lehmann, vol. 32, Philadelphia: Fortress, and St. Louis: Concordia, 1955-(hereafter cited as LW), p.11, cited by 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66, p.6.
[8] LW, 23, 236 cited by A. Skevington Wood, Captive to the Word ,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9, p.144.
[9] WA, 40, iii, 254, cited by Wood, Captive to the Word, p.143.
[10] Ibid., ii, 52, cited by Wood, Captive to the Word, p.145.
[11] Cited by M. Reu, Luther and the Scriptures, Columbus, Ohio: Wartburg, 1944, p.28.
[12] Cited by Herman Sasse, This Is My Body: Luther’s Contention for the Real Presence in the Sacrament of the Altar, Minneapolis: Augsburg, 1959, pp.109-10.
[13]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79.
[14] Ibid., p.78.
[15] Reinhold Seeberg, The History of Doctrines, vol. 2 , Grand Rapids: Baker, 1977, p.300.
[16] 罗杰斯和麦金在一处脚注(p.133, n.115)中,并不理会这类二手材料,尤其是拉吴的作品,而是引用了奥托· 海克在其《基督教思想史》中对路德的无误观的简单讨论。(Otto Heick: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vol. 2,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65, pp.347-48.)海克列举的路德认为的经文错误与瑟伯尔所列的类似。海克没有提供任何他反对拉吴作品的证据。拉吴是知名的路德宗学者,曾仔细分析过据称有误的圣经经文路德在表述时的上下文。拉吴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地显明,瑟伯尔、海克以及罗杰斯和麦金所引用的段落事实上并不显示路德认为圣经有误。
[17] Althaus,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6.
[18] Wood, Captive to the Word, p.144.
[19] Reu, Luther and the Scriptures, pp.65-76, 103. 也参 Montgomery, “Lessons from Luther,” pp.88-90,其中有对库伊曼(Kooiman)作品的评论;他总体上赞许其观点,但也让我们警惕他牵涉到圣经无误时的观点。.
[20] LW, 22, 218-19.
[21]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87; Kooiman, Luther and the Bible, p.228; Althaus,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82.
[22] LW, 22, 218.
[23] Ibid., 219.
[24] Cited by Reu, Luther and the Scriptures, p.85.
[25]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88.
[26] WA, 33, 144, cited by Kooiman, Luther and the Bible, p.235.
[27] John Calvin in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vol. 23, p.70 as cited by John H. Leith, “John Calvin-Theologian of the Bible,” Interpretation 25 (1971): 341.
[28]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ed. John T. McNeill,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vols. 20 and 21,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0 (hereafter cited as Inst.), I, vii, 1.《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七章,第一节。
[29] Inst. IV, viii, 9. 《基督教要义》第四卷,第八章,第九节。
[30] Ibid., III, ii, 6.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二章,第六节。
[31] John Calvin,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Psalms, vol. 4, Grand Rapids: Baker, 1979, p.480.
[32] John Calvin,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ed. D. W. and T. F. Torrance, vol. 10 ,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4, pp.329-30. 加尔文并非否定圣经使用人类作者,他也不是在教导机械默示论。他是说神是圣经的每个部分的终极来源,所以我们接受每个部分都应该好像是接受上帝自己那样。他拒绝圣经中含有人类的错误的观点。
[33] Corpus Reformatorum: Joannis Calvini Opera Quae Supersunt Omnia, ed. Guilielmus Baum et al., vol. 55, Brunsvigae: Schwetschke, 1863-1897 (hereafter cited as CR), col. 441, cited by Leith, “John Calvin …,” p.343.
[34] Calvin, Comm. on Psalms, vol. 5, p.20.
[35]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99.
[36] Ibid., p.108.
[37] Ibid., p.109.
[38] Ibid., p.110.
[39] Ibid., p.112.
[40] Ibid., p.110.
[41] 加尔文《新约注释》第6卷,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p.182。在拉丁文里很明显,路加不可能是归咎的对象: “in nomine Abrahae erratum esse palam est” (CR, 26, Acts 7:16 ad loc.)。旧的译本(英文)也说得很清楚“这里亚伯拉罕的名字很明显是一个错误”(约翰加尔文《使徒行传注释》第1卷,Grand Rapids: Baker, 1979, p.265)。不清楚罗杰斯和麦金所引用的来源,但因为新的或旧的英文译本都没有像他们所引用的,也许他们是根据麦克尼尔(John T. McNeill)所说的“在使徒行传7:16,路加‘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 (J. T. McNeill,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ord of God for Calvin,” Church History 28 [1959]: 143),尽管他们没有标出出处。如果这是罗杰斯和麦金引用的来源,那么他们只是重复了麦克尼尔的错误。
[42] Ibid., pp.181-82.
[43]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116.
[44] 其他关于加尔文圣经论的讨论,见Kenneth Kantzer, “Calvin and the Holy Scriptures,” 关于默示和释经,见 John F. Walvoor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7; John Murray, Calvin on Scripture and Divine Sovereignty , Grand Rapids: Baker, 1960; J. I. Packer, “Calvin’s View of Scripture,” God’s Inerrant Word, ed. J. W. Montgomery.
[45] Leith, “John Calvin-Theologian,” pp.337-38.
[46] 不清楚利思在提到现代无误观时在想些什么。看到人对无误的教义可以这样误解也是令人惊讶。知名的加尔文学者麦克尼尔(John T. McNeill)就是一个例子。他假设无误教义等同于极端机械默示论,不允许圣经人类作者的任何显著作用。(参 McNeill, “Significance,” pp.139-40, and Inst. IV, viii, 9, n.9.)但是很少支持无误的人持有这样的观点。
[47] 跟路德的例子一样,罗杰斯和麦金错误地将二分法加于加尔文(p.111)。查尔斯·巴提(Charles Partee)引用加尔文的话:“人若不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就不可能成为一位好的神话语的事奉者”,表明加尔文如何将牧者和学者从功能上和形式上连在一起 (cited by Partee, Calvin and Classical Philosophy, Leiden: Brill, 1977, p.146)。
[48] John Calvin, Theological Treatises, trans. J. K. S. Rei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54, p.130.
[49] The French Confession of 1559, Article 5. 这里和接下来对信条或要理问答的引用,都是引自 Philip Schaff, Creeds of Christendom, vol. 3, Grand Rapids: Baker, 1977。
[50] The Belgium Confession, Article 4.
[51] Ibid., Article 7.
[52] Ibid., Article 5.
[53] Zacharias Ursinus, The Commentary on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trans. G. W. Williar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4, p.108.
[54] Ibid., p.111.
[55] Rogers and McKim, The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p.200-202.
[56] 当罗杰斯和麦金简单地说“英国教会站在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之间”(p.200)犯了根基上的错误,例如,这个评估并不能反映第三十九条所表达的真正的安利甘更正教神学。同样他们奇怪地认为,英国内战推迟了经院哲学的发展(p.247),另一方面他们又断言经院哲学在大陆早在内战前就成功了。
[57] 在多特会议上英国委派塞缪尔(Samuel Ward)代表清教徒的观点。
[58] David Sabean, “The Theological Rationalism of Moise Amyraut,”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55 (1964): 213.
[59] Ibid., p.204.
[60] William Ames, The Marrow of Theology, 3rd ed. and trans. J. D. Eusden, Boston: Pilgrim, 1968, p.186.
[61]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chap. 3: “Concern for Literary Form in the Post-Reformation Period,” pp.147-99.
[62] 罗杰斯和麦金这本书的这一整章需要被彻底审查,因为它对所讨论的问题作的指导根本不可靠。例如,他们关于多特会议的三个段落(pp.164-65)包含几个错误。他们说多特生产了“信条”,但会议实际只是接受了某些法典作为《比利时信条》和《海德堡要理问答》中一些条款的权威性解释。他们宣称多特“据说要定义加尔文主义的基本要素”,但多特法典从未设想超过改革宗对阿米念主义的五个错误的具体回应。它从来没有打算总结加尔文主义的基本要素。罗杰斯和麦金称大会是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和学术化的,尽管他们承认堕落后拣选的温和加尔文主义者在大会中占主导地位。同时,信经显然用的是教牧语言并不是学术语言。罗杰斯和麦金先生断言,多特在“学术模式”上纠正了大陆改革宗神学,并提供了一个证据,即多特教导永恒的弃绝而加尔文没有教导。但事实上,加尔文清楚地教导永恒的弃绝,见Inst, III, xxii, 11 and III, xxiii, 1, 3;即《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二十二章,第十一节;第三卷,第二十三章,第一节和第三节。
[63]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147.
[64] 罗杰斯和麦金对历史圣经权威的现实威胁有一种奇怪的不敏感。这种天真也表现在他们书的引言中引人注目的判断。在那里(p.xxiii)他们似乎低估了现代主义对基督教的威胁,将经院哲学的威胁看作对美国改革宗传统的主要威胁。
[65]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p.174-75. 对此观点提供的唯一证据是图伦丁在论述圣经的部分并没有引用加尔文。
[66] 罗杰斯和麦金没有显示出他们有对图伦丁《系统神学》的第一手认识,其论述似乎完全依赖于列昂·埃里森的《加尔文和图伦丁神学中的圣经教义》(“The Doctrine of Scripture in the Theology of John Calvin and Francis Turretin,”),该文是普林斯顿大学1958年的神学硕士论文。但是即使是粗略浏览图伦丁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图伦丁的描述存在严重问题。
[67]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p.176, 179, 182.
[68] Francis Turretin, Institutio Theologiae Elenctiae, 1674, trans. George M. Griger, in a manuscript at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hereafter cited as Inst. Theo.), II, 2, 9. 本文写完后,恰好一本关于圣经论的英文翻译作品出版:Francis Turretin, The Doctrine of Scripture, ed. and trans. John W. Beardslee III,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69] Ibid., 4, 9.
[70]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176.
[71] Inst. Theo., II, 4, 1 and II, 5, 1.
[72] Ibid., 6, 5.
[73] Ibid., 4, 6.
[74] Ibid., 4, 7.
[75] Ibid., 4, 8.
[76] Ibid., 4, 9.
[77] Inst., I, vii, 4.
[78] Ibid, viii, 1.
[79] Ibid., 3, 5, 12, 13.
[80] Ibid., vii, 5.
[81] Ibid., 2.
[82] Ibid., viii, 1.
[83] Inst. Theo., II, 4, 13. 罗杰斯和麦金(p.177)只引用了这句话的一部分,歪曲了图伦丁的立场。
[84]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p.176-77.
[85] Ibid., pp.174, 177.
[86] Inst. Theo., II, 19, 18.
[87] Ibid., 5, 11.
[88] Rogers and McKim allege this i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p.180-81.
[89] Inst. Theo., II, 5, 3.
[90] From Canon II of the Formula Consensus Helvetica as printed in A. A. Hodge, Outlines of Theology, enlarged e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2, p.656.
[91] John Bowman, “A Forgotten Controversy,” The Evangelical Quarterly 20 (1948): 55.
[92] Canon III, Formula Consensus Helvetica, in A. A. Hodge, p.657.
[93]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177.
[94] Inst. Theo., II, 19, 8.
[95] Ibid., III, 10, 14.
[96] Ibid., III, 11, 11.
[97]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187.
[98] Inst. Theo., I, 7, 2.
[99] Ibid.
[100] Ibid., 6.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