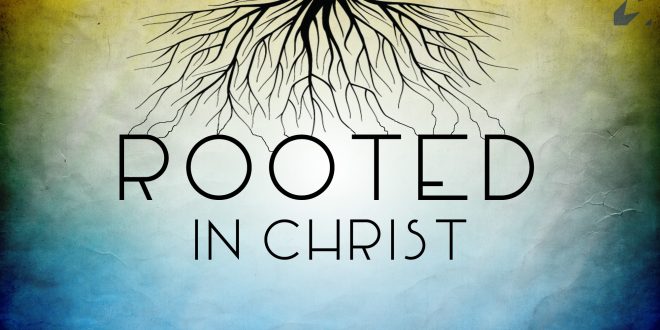文/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 译/述宁 校/尘觌 笔芯
概要
福音的教会论描述福音与教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三位一体上帝的恩典如何使教会成为一个圣徒团契。因此:1)对“上帝的完全”(即上帝之存在与作为的充分和丰满)的解释,塑造了关于教会的教义。这种完全并不是包容性的(像在某些“相通教会论”中那样),而应被视为恩典的一种行动,上帝在其中自己定意要与祂的受造物相交。2)“教会的有形性”(流行遍布于现代教会论)确切而言是一种属灵的有形性,藉圣灵的作为而拥有。教会主要的有形行动乃是见证上帝的临在与作为。
一、教会,与上帝的完全
1、福音的教会论的特征在于说明福音与教会“在互异中的关联”
福音的教会论的任务是描述福音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它的责任是去考察在哪个意义上耶稣基督的福音必然意味着某种新的人类社群秩序的存在,追问究竟基督徒共同体生活是内洽于福音的逻辑抑或仅仅是一种附属与偶然。福音与教会的关联究竟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本文给出的答案可用下述方式概括:
福音的本质在于三位一体上帝的恩典在祂创造、和好及成全的工作中所拥有的自由主权(the free majesty)。出于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一上帝自有(self-originating)的生命的丰富和无限完全,上帝定意成为祂所造之物的上帝。上帝对受造者的这种指向性,永恒地根源于圣父的旨意。圣父的心意是,从虚无中(ex nihilo)出现与圣三一内在生命爱的团契相对应的一种被造。圣子实施这一旨意,祂既是所造之物的创造者也是其再造者,祂(从虚无中)召他们成为存有,并且当他们堕落远离了这位主(他们藉祂而造也为祂而造)时,再次造成他们。而在圣灵里,上帝的这一旨意得以完全。圣灵通过托住受造者的生命、引导他们的方向以达到被造的目的(即藉着圣子、在圣灵里与圣父相交)而成全受造者。因此,“与上帝相交”乃是福音所彰显的奥秘(西1:26)。
这种彰显并不仅仅以宣告的形式出现。作为上帝对祂所造之物的旨意的彰显,它有无限的能力与创造力,它产生了一个聚集(assembly),一个社群空间(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政治和文化)。在那个空间中,“和好的福音” 所具有的转变能力,在受造者的关系和行动中变为可见。这种可见的形态不是一种简单的自然量(natural quantity),而是具有一种特殊的有形性,这种有形性是被基督和圣灵所创造,因此只有在祂们的命令下才能被觉察到。然而,福音也必然导致一种受造的聚集的形态——圣徒的团契相交(communion)。
因此,基督教信仰是“教会性的”(ecclesial),因为它是“福音性的”(evangelical)。而且同样真实的是,基督教信仰是“教会性的”,也“唯独”因为它是“福音性的”;也就是说,它的教会性唯独来源于(且完全依赖于)上帝对受造物的至高旨意在福音里的彰显。教会之所是,取决于上帝之所是并因此而有的作为。因此,福音的教会论尤其要关注的,不仅仅是阐明“教会是福音的必然结果”,而且还要阐明“福音与教会的存在顺序是严格的、不可逆转的”,即福音在先,教会追随其后。福音的教会论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在于准确清晰地说明福音与教会“在互异中的关联”(relation-in-distinction)。“关联”,是因为福音关注上帝与受造者之间的团契;“互异”,是因为即使在其相互关系中,这种团契永远是单方面恩典带来的神迹。上帝与受造者的这种特殊相遇模式,被克里斯托夫•施威贝尔(Christoph Schwoebel)称为上帝与人类的存在和行动之间“根本的不对称性”;正是这种模式,刻画了教会的组成与持续存在的特征。[2]
福音的教会论所关注的是揭示教会的必然的特征及必然的派生特征。以下是两个结论。1)若教会论完全外在于福音的解释,那么这种对福音的解释是不充分的。许多现代更正教神学和教会生活,都被这种二元论假设所破坏,即把教会的社群形式看作一种纯粹外在并且相当无关紧要的形式,一种仅仅是为了传讲圣言而有的机制,或者是为了被视为内在灵性事件的信仰提供的场合。更正教福音派的一些流派吸收了现代政治和哲学文化中的唯意志论(voluntarism)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已经造成了格外腐蚀性的影响,不仅抑制了福音里整全的教会论视野感,也模糊了我们从权威的宗教改革家及其重要的更正教继承者那里本应学到的许多东西。加尔文写道:“我们参与教会就大有能力,因这保守我们与上帝交通。”[3]2)然而,教会论不应成为“第一神学”;现代更正教中很大程度上存在的教会论极简主义,不能通过把教会论扩充膨胀为基督教一切教义之基础的方式来纠正。在过去几十年的主流更正教神学中,这种扩充膨胀很迅猛而且很成功,比如在那些从神学的“后自由主义”[4]中汲取灵感的人那里,在那些发掘出“天主教式的路德”和“天主教式的路德宗信仰”的路德宗人士[5]那里,又或者在那些用“实践”的语言来形容教会的人那里[6]。若它们强调教会是救恩计划中的要素的话,这种神学重整的尝试,以及给这类提议带来促进作用的教会生活,当然意义重大。然而,由此产生的教会论比重太大,有时会构成问题。教会论如此充满人的视野,以至于遮盖了恩典的神迹,而恩典的神迹乃是教会生活与行动的基础。
要取代这种肥大教会论的,不是萎缩的福音的教会论;这类萎缩的教会论曾是天主教批评的对象,并非毫无道理。我们在此的任务与其说是将教会摆在恰当位置,倒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在对上帝伟大作为的依序阐述中,认出教会论教义的恰当位置。下面是这一阐述的初步勾画,聚焦在两个彼此相关的主题上:1)教会与上帝的完全之间的关系,在其中说明,教会乃是圣徒的团契相交,是上帝藉祂拣选、和好与成全的工作而分别为圣的、与祂相交的人的聚集;2)作为人类社群的教会的有形生活和活动,与作为被圣言和圣灵所造的教会的无形存在,两者之间的关系。对福音真理的真正关注,需要认出各种区别——上帝与人类的区别,基督与教会的区别,圣灵工作与圣徒见证的区别。这些区别不符合绝大多数现代教会论的口味,有时它们被诋毁为“恶果”,生于那种将自然与超自然割裂的“分离神学”(按德鲁巴克的叫法)[7]。但是,显然有必要对它们作一些更深入地解释。这样的解释(在福音的约束下能够处理得当)将会表明,这些区别可以反映创造主和受造者之间的正确秩序,这种秩序在基督里被恢复,被圣灵分别为圣而成了福气,并且如今汇集在圣徒的相交中,他们快跑奔向上帝荣耀的院宇。
2、教会论的神学构建从“上帝的完全”这一概念开始
教会论是否好,取决于其基础——上帝论。这一原则无非是在断言,一切基督教教导中三一论具有首要地位,这意味着,好的教义秩序禁止教会论中出现任何不符合教会对三一上帝及其作为之特性的认信的更改。因此,就构建关于教会的神学这一任务而言,这意味着,在其教会论中,基督教神学必须格外警惕,以确保两件事:1)基督徒对上帝的认信,应当具备有效的整全视野,而不只是挑选一部分跟特定教会论提法相协调的上帝的属性或作为;2)教会论的规范,应当是上帝在祂启示中显明的特定属性,而不是教会论和上帝论中的一些常用术语(比如在当代讨论中几乎无处不在的“关系”一词)。神学在开始讨论教会论前必须暂停,以确保在关于上帝的教义和关于教会的教义之间恰当区分各自的任务。在此,不耐烦将“再次”(之前已是)萦绕我们心头。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提出从“上帝的完全”这一概念开始。教会论中主流的声音要我们从其他地方入手,最常见的是从经世三一论(economic Trinity)的教义中入手。我希望在下文论述的进程中能够清楚地表明,这样做是错误的,采用这一出发点将导致对于福音与教会之间“在互异中的关联”的误解。
“上帝的完全”是指什么呢?在我们此处的语境下,“上帝的完全”是指上帝超越的(而非道德的)伟大。“上帝的完全”不仅仅是上帝道德上的至善,而是其生命的充实性、其存在的丰满性或完全性、其整体性(以此祂乃是祂所是的)。作为完全的那一位,上帝是全然实现的,毫无缺乏,在祂自己的幸福中也没有短少任何要素。从亘古祂就是完整而持续满足的。这样看的话,“上帝的完全”非常接近于其他一些属性,例如,祂的无限性(即祂的存在和向受造物的临在毫无限制的特点),或祂的主权性(即上帝对万物的公义统治的完全有效)。然而,“完全”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指向上帝完全的尊荣,上帝在其中是祂所是。
“上帝的完全”主要不是形式概念,而是实质概念,它向我们论到上帝的生命和作为。上帝生命的完全,乃是合一与关系的丰满性(也就是爱的丰满性),即上帝永恒地作为圣父、圣子和圣灵而存在。非受生的圣父、永恒受生的圣子、发出的圣灵,在这个完全的循环中,上帝是没有起源的,因此在祂自己的生命中充满至高的生命力。祂没有从其他任何事物那里接受生命,也没有其他任何事物能改变或延长祂的生命,因为祂充满无比的生命力。而上帝作为的完全,乃是祂神圣工作的纯全性。就像上帝的生命一样,上帝的作为出于自己,因此是自我指向、自我实现的。在上帝的旨意和上帝工作的成就之间,没有缝隙或不牢靠的停顿,不存在什么时刻上帝必须得到其他代理者的协助才能完成祂的工作。在祂的自由自愿中,上帝可以选择将别的代理者分别为圣来服事祂,但这种分别为圣,并不意味着上帝有什么缺乏,而是显明祂的恩慈,祂以这恩慈、在祂的丰满中、拣选受造物让它们服事上帝而变为尊荣。上帝的工作完全自发、完全有效,破除一切阻碍,不费吹灰之力地达成其目标。
虽然“上帝的完全”这一概念乍看似乎与关于教会的教义离得遥远,但它的教会论含意其实已经唾手可得了。“上帝的完全”是祂生命与作为的充实性,但在这生命和作为中,有一种向外(ad extra)的动作或者说转向,在那里面、出于祂自己的完全,上帝定意并且建立受造物。我们该如何理解“上帝的完全”与受造界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地说,“上帝的完全”是包容性的还是排他性的?包容性的完全就是说,上帝的丰满包含了上帝以外的某种现实作为其组成部分,这样,因为被造物以某种方式被呼召参与到上帝的生命中,上帝的生命便是由它们参与其中共同构成;而另一方面,排他性的完全则是说,上帝的丰满是自成一体(a se and in se)的。上帝与异己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但它们是上帝之自由自愿的表现,而不是一种缺乏的表现,而在那样的关系中,受造物并不参与上帝的生命,而是被拣选进入和祂的相交,因此被呼召到上帝面前。若从教会论的角度,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教会作为与上帝有关系的受造物的聚集,究竟是内在于上帝的完全,还是外在地关联于上帝完全的存在和工作?上帝完全的存在是否包括了教会的存在?
3、“相通教会论”的教义罗列方式及它的形而上学基础,由此带来对教会论的破坏性影响
为了展开教会论的这些方面,我们可以首先考察过去四十年来教会神学中最重要的轨迹——“相通教会论”(communion ecclesiology)[8]。使用“相通”(koinonia)的术语来谈论教会的本质、她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她在救恩奥秘中的位置,这种做法很流行,已遍布于当下。人们普遍认为,相通的神学已经证明了它在宗派间的对话中能够发挥作用(英国圣公会及罗马天主教的热衷构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因为它明显能够提供一种关于教会本质的综合解释,在此基础上可以重新审视一些特定的宗派分歧(例如关于圣餐、教牧秩序或称义)。此外,它的教会论生根于启示和救赎的特定神学中,这给一系列基督教传统提供了资源以发展更丰富的教会论,不受所继承的传统束缚。对于罗马天主教徒来说,它提供了一种语境,其中教会的法律性概念可以与作为救赎奥秘的教会生活联系起来;对于圣公会的许多信徒来说,它使得作为合一的“标记”的“历史主教制”(historical episcopate)的神学得到了一种新的阐释;对于路德宗的许多信徒来说,它使得他们有可能抛弃所继承的教会论外在主义,重新整合关于教会和救赎的神学内容。
相通教会论并不是前后连贯的一套教义,而是对教会论、圣礼神学、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等主题的一系列多样进路的集合,它们都有一些很强的家族相似性。就我们当前的目的来说,需要注意的是相通教会论的以下两个方面:它的教义罗列方式,以及它的形而上学基础。两者都指向一个关键问题:作为受造物的交通,教会与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神性交通的完全性的关系是什么?
关于相通教义,我们可以从吉恩•玛丽•蒂拉德的 Eglise d’Eglises(对相通教义最精彩的阐述之一)中的总结开始:
在基督(其道成肉身乃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现实相交)所取得、圣灵所赐下的救恩的益处中与上帝的相交(上帝自己是三位一体的相交),以及受洗者之间的弟兄相交(重建四分五裂的人类之间的联结关系),所有这一切都通过“耶稣基督”这个一劳永逸(不可逆转)之事件里的相交成为了可能,而这个相交乃是在若干世纪以来使徒见证所保证的、圣餐(圣体圣事)所庆祝的。教会的本质便是在此。[9]
由此,我们可以将三个相互紧扣关联的教义梳理出来。首先是关于上帝的教义。基督教关于上帝的教义是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三位一体被设想为上帝诸位格的相交。因此,上帝的合一不是无差别的同质性,而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相交的丰富生命,是一种相互的、开放的相交。其次是关于救赎的教义。按上帝形像造的人,其被造的目的是进入与上帝以及与所有其他受造者之间的相交。罪是对这一终极目的的背弃,破坏了人与上帝之间的相交,因此也破坏了与其他受造者之间的相交(当今普遍的则是从个体特征的角度谈论罪)。救赎的目的是将人类重新融合在相交中,既与上帝相交也与其他受造物相交。而这一目的无法简单地通过某种外在的或宣告的形式(就如某种对于终止敌意的神圣宣告)来达到,而是以内在的方式来达到:通过耶稣基督里面上帝与人类在道成肉身上的联合。这样,圣道取得人性,不仅仅是一种达成上帝承担人罪的手段,也是上帝与受造者之间相交的恢复。第三,是教会的教义。道成肉身的相交在教会中延伸而施行拯救,因为教会内在于上帝与人类联合这一基督论的奥秘。基督论和教会论是相互牵连的。也就是说,教会不只是环绕在上帝拯救作为之外的一种聚集,也不是一个分配救恩福分的舞台;作为相交,教会乃是救恩奥秘的组成部分。在教会的相交中,救赎不只是被认信,而是被具象化;教会是被拯救的人类,是救恩的社会性现实。因此,教会作为在基督里与上帝相交的新人类的聚集,教会从本质上是一种可见的共同生活形式,是世界的历史与物质之秩序的一部分。在圣餐神学中,这意味着,不能将圣餐看成对一个缺席事件的回顾纪念,或者内在灵性转变的展示。它乃是相交:是在基督里的参与,是临在且有效(而不仅仅是被标示)的救恩。就共同体的秩序而言,这意味着,在最低限度上,职分(office)对于使徒福音中相交的公共形式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就教会与世界的关系而言,这意味着,教会的共同生活对于人类生活与文化达至完美是建构性的,并且因此相通教会论在全面解释人类社会福祉方面处于核心位置。简而言之:“我们的信仰永远不应该割裂上帝从一开始就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在基督和教会里伟大的圣事(sacramentum magnum in Christo et in ecclesia)”[10]。
到此,我们就转向相通教会论的第二个方面,即它的形而上学基础。这里的关键文本是德鲁巴克(Henri de Lubac)的作品《超自然》(Surnaturel)[11]。与大多数溯源运动[12]的思想家一样,德鲁巴克不是一位哲学神学家,而是一位对传统的注释家。然而在此书中,他持续地关注教义、灵性与哲学的边界领域,过去五十年里这部作品在天主教神学界内外产生了格外广泛的影响:这部作品与冯•巴尔塔萨(von Balthasar)和米尔班(Milbank)的作品一样充满各种各样的意象(figures),若离开了德鲁巴克开启的可能性,后者是无法完成的。对于德鲁巴克来说,相通教会论(用他的说法叫“大公教会信仰”,catholism)不仅反对“分离神学”,而且也反对“分离哲学”——围绕着一种将自然与超自然进行系统性分离的做法而构建的形而上学。作为其更加教义性的天主教对应物,《超自然》试图拆除新经院主义的教义学和护教学的大厦,德鲁巴克认为它们是在自然与恩典的二元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种二元论在教父们和托马斯•阿奎那那里都没有,并且它无情地导致了自然的世俗化及其与上帝的现实之间的疏离。自然界被单独考虑,被认为拥有一种内在的终极性、纯粹的自然目的,因此可以在(指向上帝里的参与的)任何超越性的秩序之外设想这种所谓“纯粹”的自然。由此导致的二元论——在超自然和自然之间、在时间和历史之间、在物质形式和内在本质之间——不仅使得关于受造物的基督教本体论变为不可能,并且也在教会论方面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作为超自然的基督和作为自然的教会,被置于一种纯粹外在的关系中。对应于自然哲学(即自然法、自然神学)的出现,实际上产生了一种自然教会论,是天特会议和改教家们共有的。在天主教的形式中,这种自然教会论将教会的等级与司法体系从(在道成肉身和圣餐中体现的)上帝在基督中的自我相交中剥离出来,而在更正教的形式中则导致的是一种激进的“内在主义”(internalism),按这种理解,教会的可见形式绝不外乎是为直接恩典的生发而提供的世俗场合。
从我们的主题的角度来说,相通教会论的教义学及其形而上学基础共同引发的核心问题是:一种从“上帝的完全”的神学出发的教会论,是否从一开始就将德鲁巴克所试图揭露的、无情地导致教会论外在主义的腐蚀性的二元论植入了自身?作为回应,我的提议是,福音的教会论并非只能在相通教会论与(德鲁巴克及其他人颇有见地试图清出现代基督教的)激进的二元论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一种关于上帝与受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教义为我们开启了一系列新的可能性。这种教义试图阐明上帝和祂的人类伙伴之间的差异,而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遭到自然主义或外在主义的传染,而是因为创造、和好之类的神学要求我们将上帝和受造者的关系视为一种“在互异中的关联”,那就是,圣约团契(covenant fellowship)。
4、教会论是圣徒被拣选之教义的结果,因此教会论中的第一表达就是宣信“圣徒相通”
教会论的发展不能在上帝与基督的完全上做出妥协;但是,如果严苛地将教会从救赎计划中排除出去,神学就实际上无法让自己避免这一妥协。所需要的不是将教会论削减至消失,而是更准确地说明上帝的完全,由此产生关于团契相交的教会论。因此,我们必须回到上帝论。
上帝是完全的,但祂的完全包括一种向外的行动,一种转向(非上帝的)事物的行动,而上帝是它们威严的创造者、调解者与成全者。关于这一完全奇迹性的、佳美得无以言表的转向,我们至少需要谈论以下三件事。1)这不是上帝之存在的第一行动,而是第二行动。第一行动是圣三一的永恒流动的安息,是圣父、圣子与圣灵的生命、平安和爱。这是上帝(尊荣的)充实性的行动。与这一行动相对应的,是进一步的行动,其中上帝的完全构成了祂生命之外的某种现实的根源和持续基础:“……之外”不是无关,乃是拥有作为上帝之赐予的完整的自身存在,而非上帝的自身存在的一种延伸。这由上帝愿意并白白供应受造物之存在的行动,是一种必然的行动。它不是外在的必然,因为那样它就不是上帝的行动,而是上帝的反应(因此就不是属于上帝的)。毋宁说,它乃是内在的必然,因为它也在第二行动中从上帝永恒的计划中流淌出来。2)这种行动是神圣之爱的行动。上帝神圣之爱是一种完美的纯全,祂以此将受造物分别出来与祂自己相交。祂将它们分别出来,首先乃是通过定意要有受造物,然后是通过创造它、维持它、使它与祂和好、引导它达致完全。上帝的神圣充满爱,因为这神圣并不是上帝的一种纯粹的自我隔离,而是上帝自己选择在与非上帝之事物的爱的团契中如此纯全;上帝的爱是神圣的,因为它使受造者成圣,好与那至圣者相交。3)因此,这种行动最准确、最根本地说,是上帝恩典的行动。恩典乃是指向受造物之福祉的主权。上帝的主权(祂毫不间断、毫不费力的统治)的完全,乃是完全为了受造者的益处。藉此,上帝意愿、准许并滋养受造者的存在,如此赋予生命。
因此,在神圣之爱与恩典的第二行动中,上帝的完全实际表现为祂对于团契的决定。正是这一行动,构成了教会的基础。教会存在的基础,正是这简单而又无法测度的上帝的宣告:“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以教义表达就是:教会论是圣徒被拣选之教义的结果,因此教会论中的第一表达就是对圣徒相通的宣信。相应地,团契相交是一个派生的教会论概念,是拣选与神圣这两个双生概念之作用的结果。这种理解保存了上帝的完全性,因此保存了教会与上帝的区别,而这种区别乃是团契的首要条件。
然而,在展开这些教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们从教会论语境下的一些更被熟知的用法中抽离出来。虽然神圣作为教会信条的标志,其地位已经确立,但它在现代讨论中引起的讨论相对较少,特别是在普世主义教会论中,合一性、大公性和使徒性通常是位居前列的论题,因为它们乃是宗派分歧的标志。讨论教会的神圣性,则通常是在成圣(sanctification)问题的语境下[13]。然而,恰当地说,作为教会之成圣的神圣性,只是教会神圣性的一个从属方面;从根本上讲,当说到“教会是圣的”时,实际上是指,教会是选民的聚集。成为圣徒,就是成为被上帝呼召说“你要作我的子民”的人。教会的神圣与她被拣选之间的这种关联,反过来又要求我们重新关注拣选教义在教会论中的运用。在高派更正教正统(high Protestant orthodoxy)中,拣选几乎完全只与上帝之选择的高深难测有关,这意味着拣选在教会论中被用来强调:单单拥有可见的、“混杂”的教会中的成员身份并不确保永生的安稳。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拣选的道德化或主观化,并将之局限于基督徒自我身份的场景中。这种“隐藏的自然主义”[14]大大扭曲了事实,因为它将对上帝的确定性变成了一种焦虑。最准确地说,拣选涉及的是上帝的存在对我们满有主权的指向性,即上帝自己定意为祂自己而召唤、保护、赐福一群人。简而言之,教会“建立在上帝的拣选之上”[15]。与神圣一样,拣选教义的教会论力量乃是为了强调这一双重真理:与上帝之团契的根源在于上帝,以及,上帝指向那作为“上帝自己的子民”的教会。
那么,“我们信圣徒相通”这一教会认信是什么意思呢?1)在关于教会的神学讨论中,我们其实是处于信仰告白的领域。对教会之存在与本质的真正理解,不可能通过对其自然历史的考查而得到,只能通过对上帝拣选与分别为圣之工作的认识而得到。教会藉着上帝这工作而存在,她既不具有天然自发的生命根源,也不具有内在的能力来保持自己属灵团体的身份。教会作为受造领域(在其中我们与上帝相交)的这一性质,完全出于上帝的拣选与分别为圣的临在。因此,只有在对上帝的工作及其方式的信仰认识中,我们才能看出教会的真实面目:圣徒的团契。用正式的术语来说,“教会”这个概念不能从“社会性”(甚至基督教社会性)的概念中推导出来,也不能归结为“社会性”。虽然圣徒的生活必然是一种社会形式,但之所以如此,只因为上帝的拣选与呼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认信圣徒相通不过是在重复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认信。2)所认信的内容是“圣徒”的相通。上帝的圣徒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构成了一个人类的聚集,其存在完全基于上帝的决定,而不是基于受造者的声望。“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申7:7-8)上帝的拣选在救恩的工作中实施,拯救一群百姓脱离彻底的危险而将他们聚集起来(……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申 5:6;从“算不得子民”的处境下被呼召进入“作了上帝的子民”的处境,彼前2:10,何2:23)。上帝那拯救的作为使新造的上帝子民区别于其他所有的可能性,因为分别为圣的工作使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存在方式,离开这位上帝就是回到“不是我的子民”的状态。这样,拣选将这子民置于上帝赐福的领域内,因为拣选是关乎生命的一种定意。而如此被拣选蒙受福分的子民,乃是被呼召去顺服上帝、按照圣约子民的身份本质遵行律法(那指定的样式)而生活。与作为“分别为圣”(consecration)的圣洁相对应的,是作为“积极的神圣性”(active holiness)的圣洁。3)教会认信的内容是圣徒的“相通”。拣选产生一种政体(polity),一种共同的生活(common life)。然而,这是一种独特的共同生活,而不只是一般的社会性的某种调整。这是圣徒的相通,故其生命的每个方面都被上帝那带来和好的作为所产生的冲击波而决定。它是重生的、末世性的相通,是经历改变的共同生活。这一相通的政体之核心,乃是一个无法被同化的事件与临在,而这相通共同体既不是它的延伸,也不能参与其中。那个事件与临在,就是共同体的主、居于共同体中的至圣者完全的存在和作为。
但是,有那位至圣者居于其中的人类共同生活,是指什么呢?特别是:这种共同生活如何与它的主相关联?那位至圣者与圣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因为这种关系被理解为“互异中的关联”最合适,所以教会与她的主之间的“相交”最好被表达为团契(fellowship)而不是参与。在此,加尔文对基督与教会之联合的解释,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对加尔文来说,这种联合的存在,乃是一个深刻的福音真理:
因此,元首和肢体彼此的联合,就是基督居住在我们心中。这神秘的联合对基督徒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事,因为我们一旦拥有基督,就享有上帝赐给基督的恩赐。所以,我们并不是因为从远处观看基督而享有祂的义,而是因为我们穿上了基督,所以也被接在祂的身上。简言之,我们之所以称义是因基督喜悦使我们与祂自己联合,由于这缘故,我们因享有基督的义而夸耀。[16]
但是,这一“义的团契”绝不是粗俗的全然混同(crassa mixtura)——加尔文所厌恶的、阿西安得(Osiander)所认为的那种神性与人性的简单混合体[17]。它乃是“属灵上的联结(spiritual bond)”[18],而不是“本质性的内住(essential indwelling)”[19]。也就是说,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一种团契,在这团契中,距离或差异就跟联合一样是本质性的,因为这团契是这样一种相互性的秩序——一个在先、一个后继,一个给予、一个接受,因此排除了任何的同一性。后来在《基督教要义》中,加尔文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极为精炼的三一论的陈述:“一切藉着圣灵重生与基督有交通的人,都是上帝出于祂的慈爱分别出来作为自己产业的,只要我们是其中的一分子就与这大恩典有份。”[20]
在此有基督论方面的一些分支问题,我们很快会转而讨论它们,但在此之前,我们不应该忽略,除了准确地厘清“相交”一词的细微差别之外,还有更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其核心涉及到上帝与受造者的正确关系。因此,正如在基础教会论中常见的那样,本体论维度不得不再次引起我们的关注;那些很大程度上依赖“相通”概念而建立的各种教会论,通常在上帝与受造者之间的本体论差异上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理解。
教父们关于‘神格化’(theosis)的概念,最准确精炼地再现了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造物主和受造者之间的差异确实是绝对的和永恒的,但恰恰因为上帝是无限的创造主,所以受造者被应许参与到造物主的生命里的方式和程度也是没有限度的。[21]
若是站在这样一种优势地位上看,强调那位至圣者与圣徒之间的团契(而不是相互参与)简直就是在重复一种本体论的错误:上帝和受造物的关系被看作是外在的,因此是竞争性的,以至于他们被看作是构成反比而非正比。不过,这里混淆了太多的东西。因为一方面,“从虚无中创造”(creatio ex nihilo)的教义的一个基本蕴涵就是上帝与受造物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构成反比,然而另一方面,这一事实并不否定上帝与受造物之间存在的任何关系。更确切地讲,首先,这一事实是在说,在上帝与世界之间各样互动中的关键时刻(建立祂的圣约、取得肉身、圣子得荣耀以及圣灵的沛降)之中,上帝独自行动。其次,这一事实是在说,即使当上帝使自己联合于圣徒团契,即使当上帝通过教会施展作为,那位至圣者与祂的圣徒之间的分界线也没有被逾越。上帝可以选择通过受造者来行动,如此祂抬举了这一受造者,但祂并没有赋予这受造者恒久的能力,而是将其分别为圣以完成特定指派的任务。在受造者的行动中,它仍然完全保持从属性、服事性、指定性。因此,教会论中的本体论规则是,无论上帝和祂的圣徒之间存在什么联结,这种联结都是在一种更大的“相异性”中去理解的。简言之,那就是圣徒与主(那位至圣者)之间相交的含义。
总结一下以上的内容:关于教会的神学需要得到关于上帝之完全性的神学支持,达到这一目的乃是通过将教会论与拣选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对教会的理解——与上帝之间的有差别的、不对称的团契。最后,我们来讨论与教会有关的上帝之完全性的基督论层面。
5、根据基督道成肉身、救赎和升天之教义,若“完整的基督”取消了基督与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间的区别是不可接受的
迈克尔•拉姆齐(Michael Ramsey)在其早期的杰出著作《福音与大公教会》(该书与德鲁巴克的《天主教教义》都是上世纪教会论方面的权威文本)中,以其特有的精炼和说服力论证说:“教会的意义和基础见于耶稣的死和复活以及在这些事件中门徒奥秘性的分享。”[22]然而,“教会在基督里分享”这一概念能否与对上帝之完全性的断言相互协调呢?我们能否和拉姆齐一起说“教会的历史和圣徒的生命乃是弥赛亚生平里的作为”[23]呢?
反思的第一个思路涉及到道成肉身的方式。道成肉身是一次完全独特、完全不可逆转的上帝的行动,在这一行动中,上帝的儿子使自己联合于耶稣这个人(in it the Son of God unites himself to the man Jesus)。道成肉身是独一无二的,并不是某种更一般的神人联合而成的人物。道成肉身的起源完全在受造物的能力范围之外,道成肉身之前在受造物中也从未存在任何对等事件。因此,耶稣的人性不是被上帝吞并或征用的受造量(creaturely quantity),否则它就先于道成肉身而构成其受造先决条件。道成肉身是单方面的,它依赖于上帝之存在与行动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此外,因为它是不可逆转的,所以道成肉身也不可延伸。它断然不同于(比如说)上帝在受造物中及通过受造物的护理性临在,在其他现实中也没有与之类比或重复的事件。没有什么能限制它显著的独特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道成肉身的联合是个人性(personal)或说位格性(hypostatic)的联合,而不是神性和人性的某种一般联结中的本质层面上的联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道成肉身的完全性。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基督人性的真实与完整,而不过是具体说明道成肉身发生的条件。这也不是否认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和我们的同质性。上帝在基督里使祂自己与我们联合,但祂也唯独在这一位里如此做。而这一位并不是某些更一般的相交或同一的标志。祂乃是唯一的中保,唯有祂是上帝与受造物之联合所发生的地方。但这是什么性质的联合呢?它是这样的联合:基督在其中选择和我们分享与上帝团契的益处。祂作我们的调解者,亲自承担了我们与上帝的疏离,并如此将其除去。祂取了我们的人性,但这并不是通过把它吸收到祂自己里面以使我们能分享祂与天父的联合。祂取了我们的人性,乃是通过自由自愿地代替我们,取了我们的位置、存在和行动。祂的人性收聚其他所有人到祂自己里面,只不过是为了代替他们。祂的人性囊括了所有人在它里面,但这仅仅在祂同时也排除了所有人这一意义上成立。作为基督与祂身体之间婚姻联合的教会的奥秘,谈论到这一点时不管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意味,都不可能意味着道成肉身之独特性的缩减。
第二,基督的完全性,是在祂的死和复活中彰显的。与道成肉身的“独生子”(filius unicus)相对应的,是救赎论的“唯独基督”(solus Christus)。在救恩的奥秘中,基督独自行动,祂的行动具有终结性和全备性。祂那一次行动,是教会无法重复的,因为没有任何必要。当然,道成肉身的圣子的死和复活构成了通过洗礼所表明的教会之存在的形象,这是无可辩驳的。但教会的死和复活完全取决于其主人的、无法被代表的死和复活。只有当我们仅仅把教会的道德生活行为看作基督拯救性介入的一个微弱类比时,我们才可能谈论教会“进入基督自我奉献的举动”;不过,作为与圣餐有关的主题时,它隐秘地破坏了基督位格和工作的异质性特征,并因此在基督位格和工作的完全与恩典上产生妥协。
因此,第三,复活和升天具有重大的教会论意义。基督的复活和升天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指出了基督和祂的圣徒之间存在着合宜的距离,即使圣徒是“在祂里面”。基督在复活节以及在四十天后的升天,表明了祂与教会之间的鲜明对比。教会与基督一同复活,但她并非如同基督那样复活。基督自己在升天的时候合宜地离开,这标志着祂作为圣徒敬拜的对象、坐宝座的主的超越性。当然,圣徒与祂一同活过来,并且是复活与祂一同坐在天上(弗2:5-6),但在此的基本原则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弗2:5)。即使教会与祂一同复活并与祂一同坐在天上,她也只是作为复活之恩慈的产物并主掌管的对象。加尔文说:“……称基督为元首极为妥当,因为唯有基督以自己的权柄和自己的名作王……” [24]加尔文反对人僭越救赎主的权柄(这种僭越可能伴随着教会教牧秩序方面的某些观点),但这背后是关于基督之完全性的神学,在这一神学中,基督作为复活升天、在圣灵里显明其福气(benefit)的主,即使祂进入与教会之间的亲密团契,祂也超越教会。
这样,综上所述而有的主张是,若“完整的基督”(totus Christus)(把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囊括其中的基督之完整性)这一概念取消了基督与祂怜悯之对象间的区别,那么这个概念不可接受:根据基督道成肉身、救赎和升天之教义来看,不可接受。德鲁巴克说:“基督在祂里面承担了所有人……因为道并不仅仅取得了一个肉身;祂成为的肉身不是简单的合体(corporatio),而是……共合体(concorporatio)。”[25]在这一点上,负责任的福音的教会论应该表达出不同的意见:任何试图综合基督论和教会论的做法必须用“独一的创造主(unus solus creator)这打破一切的真理”[26]来打破。基督的完全不是综合性或包容性的,而是一种在自己里面的完整性,并且只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圣灵的工作延伸到圣徒,这位圣灵将祂“极丰富的恩典……祂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弗 2:7)分享给我们。
但这不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实质上消极的教会论,一个在世上没有持久、活跃之形式的教会吗?是否存在一种真正的教会论(作为水平维度),对应于道成肉身和救赎论(作为垂直维度)?是否存在圣徒的有形历史?
二、有形见证无形
1、对教会的无形性恢复一种恰当的意识,当代教会论才能得到良好发展
“基督的身体在尘世这里占据了物质空间”[27]——这是朋霍费尔在《作门徒的代价》里关于“有形的教会共同体”的一系列精彩反思的开场白。最近大部分教会论的共识已经对朋霍费尔判断的正确性予以肯定:如果不把教会的有形性放在首要地位,就没有合格的教会论。但在这里,我提出基于福音的一个相反意见(sed contra):假如对教会的无形性(即教会有形生活的“属灵”特征)恢复一种恰当的意识,而不是聚焦在一种作为实践性有形团体的教会,那么当代教会论才能得到良好发展。此外的一个推论是,要真正理解教会的积极生活,并不是把它看作对上帝之临在的有形的实现或表达,而是对上帝在基督里的(如今势不可挡地在圣灵能力中临在并作用的)作为的见证。教会的“属灵有形性”,以及教会行动的特征乃是“见证上帝”,这两个重点组合在一起,反映了对上帝之完全与受造物之存在和活动之间关系的一种有序解释,对上帝与人类的关系既不割裂也不混淆。教会是由福音所产生的人类共同生活和行动的形式,以见证三位一体上帝完全的话语和工作。
就像“相交”的概念一样,“有形性”的概念在当代教会论中非常普遍[28]。“转向有形性”(无论是在普世教会运动对有形合一的关注中,还是在运用“社会实践”的相关概念来描述教会的过程中)显然对我们在这里提供的、指向上帝完全性的教会论概述提出了重大的问题。最迫切的问题是:一种由上帝之完全性的神学所支配的对教会的解释,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削弱教会的社会和历史的物质性,尤其是鉴于它的教会本体论扎根于时间之前的拣选以及道成肉身之圣子的不可参与的位格和作为?这难道不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教会的某种“属灵化”(教会的社会形式外在于它的存在,而它的公共生活被世俗化或自然化成了许多堆积的碎片)吗?这难道不会导致压倒性地强调教会的被动性(教会与基督的行动实际隔绝,教会永远只是接受者)吗?那么,教会难道不就仅仅是一种虚无,由作为异质力量的纯粹的恩典侵入时间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虚无吗?简而言之:这会给教会的有形性带来什么影响?
2、唯独通过圣灵的工作,教会才成为有形
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明确:问题不在于教会是否有形,而在于教会有哪种有形性?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关于上帝的完全,关于拣选,或关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独一功效与充分——都不应该被看作是在否认教会的有形性。然而,需要对有形性的概念进行谨慎的教义厘定说明,以确保它与基督教对上帝的认信显然一致。这个厘定应该包括对这两方面的解释:教会的有形性是“属灵的”有形性,教会的行动是对上帝话语和工作的见证。
“有形”的教会是“现象”的教会:具有作为人类活动的形式、形状和持续性,并作为一个社会项目而存在于世界历史。教会在这个意义上是有形的:她是一个真正的受造性的事件和聚集,而不是纯粹的末世性的政体或文化。她是男女老少因为福音而做的事。教会是一个人类聚集,她参与在人类的活动中,她有习俗、文本、秩序、过程、财产,就像其他任何的有形社会实体一样。但是她如何进行及拥有这些事物呢?她藉着圣灵的工作而进行并拥有这些事物。只有通过圣灵的允准,教会才成为一个人类聚集,因此教会也唯有藉着同一位圣灵才是有形的。
圣灵是通过重生和供应其人类信使来完成和好的工作的那一位;通过这种方式,圣灵成全了受造者,使他们达致被造的目的。和好的工作是“三一”的,它深深根植于圣父的永恒旨意中,圣父立意让受造者进入与祂的团契。圣子击退一切受造者的抵抗,在对深陷不幸的受造者的怜悯中,实现了这一旨意,克服了我们与上帝的疏离,使我们与上帝和好。然后,圣灵的职分则是将救恩的益处实施在受造者身上,也就是在被造世界的时空中实现受造者与上帝及与彼此之间的团契(受造者与上帝和好正是为此)。圣灵成全受造者、使他们成圣,以使他们取得圣父所计划、圣子为其实现的样式,如此(按照信经的认信)圣灵是“生命的赐予者”,因为受造者只有在与那创造和护卫生命的上帝的关系中才能“拥有”生命。但作为生命的赐予者,圣灵也被认信为“主”。祂通过超越的自由的作为,来成全受造者。祂不能被当作一种内在的生命力量而塞入被造世界的因果关系中。祂始终是圣灵造物主(Spiritus creator),通过祂临在之事件,祂更新受造物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受造之存在的某种连续性基础。圣灵是教会的上帝。
教会教义植根于圣灵教义,这一点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它确保救赎计划的第三个要素(即在人类生活和历史中达成和好),与第一个要素(圣父的旨意)和第二个要素(圣子成全旨意)一样,都是上帝的作为。在教会论中,其实是在上帝的完全性和主权性的范畴内。如果上帝的第一和第二步的作为都是纯粹的恩典,祂的第三步作为就无疑不能是上帝与受造者的协作。上帝和好的旨意和行动在受造者领域中的实施的历史——即教会的历史——乃是新创造的历史,即死人复活的历史。“祂叫你们活过来”。(弗2:1)这种纯粹的恩情(gratuity)是教会存在的基础:教会之为教会,是因为上帝在圣灵里已经完成了祂拣选与和好完美衔接的工作,并完成了将教会聚集在自己这边的旨意。因此,教会是自然历史仅仅因为它是属灵历史,由圣灵之恩典塑造的历史。教会的有形性也是如此:唯独通过圣灵的工作,教会才成为有形,因此它的有形性是一种“特殊”的或说“属灵”的“有形性”,由圣灵创造并由圣灵揭示。[29]
更详细地说,教会有形性的根源在其本身之外,是在于圣灵源源不断地临在。因此,教会的“现象性”的形式只有在关涉到圣灵的自我赐予(self-gift)时,才是“教会”的现象性的形式。教会生活的现象,其语言、仪式、秩序、历史及其他,不是自动地(仿佛本身就有功效)构成圣徒的相交。毋宁说,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是因为圣灵使形式具有生命力以标示上帝的临在。但是,如果可见的现象自身不是教会的最终真理,那并非仅仅因为它们是现象所以就是不属灵的、世俗的、纯粹的自然事物,而是因为它们是这样一种现象:作为一种标记,它们指向那将基督带到教会与世界从而实现圣父旨意的圣灵。因此,如果教会的现象确实是教会的有形性,那么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信徒的血肉共同体中上帝之统治的真正显现”[30],而是因为它们藉着圣灵被分别为圣,作为上帝临在和作为的见证而被接纳以服事上帝。
因此,关于教会的知识不能从它有形的现象和实践中根据推断而直接得到。只有通过圣灵的能动性,才能将这些现象正确地把握为“教会”的现象。正如上帝被认识那样,教会被认识,乃是在上帝自我相交的临在所带来的知识中,而与之对应的是人的信心。唯有在这样的属灵知识中,教会才被认出,其现象才能按其所是被理解。当然,信心并不是去觉察在教会有形行动的自然历史现实背后一系列别的什么“隐蔽”现象,它乃是按其所是地理解这些有形行动:对上帝的见证。加尔文写道:“……无须……藉眼见或手摸。”[31]为什么?不是因为在僵死的自然背后,隐藏着真实的、超自然的、无形的、不可触及的教会。事实上,上帝选择只在教会有形的人类器皿(例如在教会教师的声音)中被人听见,加尔文也绝不是对感觉与灵性作任何原则性的割裂。确切地说,教会之所以在信心的洞察下有形,是因为教会正是在面向信心时走出了历史现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并且作为圣灵的创造而彻底并合宜地被看见。“其实这合一属于信心的范围就提醒我们当常默想之,无论就环境来看明显不明显。”[32]
因此,教会的有形性是一个属灵事件,要在属灵意义上认出。这不是为了支持教会论的偶因论(occasionalism),仿佛教会缺乏一种持久性的身份,仅仅由一连串谨慎的时刻组成(在这些时刻中圣灵从上头抓住僵死的形式并赋予它们临时的活力)。这样的话就是在否认圣灵确实被应许、确实被赐予教会。但问题是,圣灵如何被应许、如何被赐予?不是以某种形式被转化为内在于教会的东西,或者教会在其行动中填满或实现的东西。圣灵乃是作为主以及生命的赐予者,被应许和赐予教会。作为主以及生命的赐予者,祂区别于教会,祂是教会所信靠的那一位,祂是教会顺服的对象,教会必须为祂降临之事件而祈求:来啊,圣灵,创造之主(Veni, Spiritus creator)。
总结一下:通过圣灵的工作,教会是有形的。教会的生命和行动是圣徒团契的生命和行动,它们乃藉不可见之圣灵的生命力量而有,并通过不可见之圣灵的启示力量而被如此认出。这种关于教会有形性的解释,意图控制自己不致偏离教会论的基本性规范,即上帝在对圣徒的工作中的完全性。这种完全性在圣灵论里就如在其他地方一样真实有效;圣灵的沛降(祂在圣徒共同体中恩慈的降临),并不与圣灵的纯全相冲突。而这种规范并没有试图割裂内在与外在以至于将教会设想为世俗,它只是承认,圣灵赐予生命和启示的运作是教会之存在(其中包括教会在受造世界的时空中的有形性)的基础。
3、教会的积极有形性在于见证那一位作为创造者、调节者、成全者的上帝的话语和工作
如果这是教会“在尘世占据空间”的方式,那么关于教会行动的基本样式,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教会拥有什么“类别”的有形性呢?我想探讨的设想是,教会的积极有形性在于见证那一位作为创造者、调解者、成全者的上帝的话语和工作。[33]在谈到教会的行动是作证或者见证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教会有形的事工与它们在上帝完全的工作中的基础之间是什么关系?鉴于上帝恩典的完全,并鉴于教会自身存在于那恩典中这一事实导致的特殊有形性,见证的概念试图表达的是:教会的工作永远只具有派生特征。
我们可以回到拣选教义来解释这个问题。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彼前2:9)。教会藉圣子的宣告而存在,其中圣父永恒的决定得以实现:“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约15:16)既是这样,教会就是根据某种特殊的动力(dynamic)或行动来刻画的。这种动力是教会的源头,它出于圣父的决定,其旨意在圣子里安排,并通过圣灵的工作在人身上带来结果。它出于圣父的决定,这就赋予教会作为被拣选者而有的特定特征和动力。上帝的拣选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背景或初步现实(即或许构成教会的根基或起源,却不构成解释教会之实际所是的有效因素);恰恰相反,被拣选者的动力决定了那将教会显为有形的共同生活和活动的模式。教会的生命形式、她的主要活动(她在时空中行事的所有方式),都必须是为了见证上帝。
见证(testimony)乃是在惊诧之中向外指示。被上帝在基督和圣灵里的那全然扭转性的恩典所抓住的教会,不过是在指示某个对象。教会与她所见证的对象并不对等也不连续,否则她的见证就是自我见证,从而是虚假的。她的见证也不是一种对她所指之对象带来影响的行动。教会的见证是一个标示性的(而不是产生实际效应的)记号,它指明它所见证之对象自身内在固有的、已经实现的有效性。教会严格地隶属于她被任命授权去指明的对象,她被兴起却并非为了参与、延伸或实现一个完全在她以外的事实;如此,教会高声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正如巴特谈到施洗约翰(可能是他最喜欢的圣经人物)时所说的那样:“正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见证人,他只谈及另一个人。他没有自我存在。他自己没有重要性。他只有在见证另一个人并将人们的目光从自己身上引向那个人时才发挥作用。”[34]至关重要的是,教会的行动所指向的不是什么停滞的(即锁闭在过去或超越性中的)东西。教会指向三位一体上帝在先的完全性。她见证了圣父上帝全能有效的旨意,这旨意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突破了诡诈与敌对的疆域,如今在祂复活的临在中极其真实、无限踊跃,并通过那在基督之灵里的扭转性的力量而发动。教会是这一切的见证。
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发展关于教会有形行动的神学,其中的优势相当明显,即避免将能动性从上帝转移到教会身上。这确保了关于教会行动的这样一个概念:上帝的工作不是有待完成的现实,而是具有不受约束、自我实现之力量的一个已完成的事实(perfectum)。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将教会缩减为纯粹的被动,以至于她唯一有形的特征就是虚空,等候上帝自我呈现的话语。见证是一种人类活动,为服事上帝而做。如果教会完全严肃地对待她所要见证的,那她就不会懒惰或不负责任,这是因为福音是一种召唤。但这召唤乃是召唤人们按照福音真理所塑造的特定方式来行动。这意味着,教会被委派去开展有形的活动,而这正符合一个既定的事实——世界是三位一体上帝先在的恩典完全得胜并得荣耀的领域。事实上,按这一既定事实而行动就是:思考、说话、判断、聚集、庆祝、受苦、医治、分享、祝福。但这些行动的中心不在自己里面,这些行动也没有纯粹的自发性。这些行动来自于对上帝在基督里并如今通过圣灵而临在的作为的信心与盼望。这些行动完全由这样一个基本陈述所定义——“至圣者在你的中间”,而这一陈述是关于教会的所有其他陈述的基础和条件。教会依赖着另一位的存在和作为,教会所依赖并且不断转向的那一位,就是教会的行动的激发者和见证的对象。
4、教会见证福音,所要做的只是让圣言按其所是地呈现,并且因此让自己被置于其支配之下
教会见证福音的具体形式是宣讲圣言和施行圣礼。在圣言和圣礼中,教会表达出永活的耶稣基督的临在与活动。圣言和圣礼不是耶稣基督工作的“实现”,因为祂在圣灵里是自我实现的。确切地说,圣言和圣礼是指向祂的存在和工作,这工作已经以君王的自由和完全的有效性实现了,并且如今这工作放在教会面前,满有扭转性的力量。圣言和圣礼是教会的有形行动,它们让上帝自己施行作为。
在此我无法详尽论述关于圣言和圣礼的神学。我想只对教会中的圣言事工发表一些评论。这样做并不是要跟随那种已经依附于一些福音派传统的圣礼极简主义(sacramental minimalism),这种极简主义经常被倡导以回应令人感到繁复的圣礼主义,但它对于教会在福音里的展现有着深刻的破坏作用,并经常伴随着缺乏活力的道德化的基督信仰。确切地说,我之所以专注于圣言,是因为现代的普世主义教会论极少对这个主题感兴趣,反倒倾向于集中力量关注其他方面,比如圣礼(特别是圣餐),比如关于教牧秩序的神学。这样的结果之一是促进了一种关于教会的神学,其中圣言事工在理解教会行动的特征上不总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圣礼的执行通常被认为是教会行动的范式;而关于上帝的工作与教会的工作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通常是藉着试图梳理一系列圣餐神学相关主题来讨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对于将圣餐的“牺牲性”特征视为教会根本行动的讨论)。结果是,“圣餐教会论”成了不证自明的规范;而我希望能稍纠正得平衡一些。
在启示录的开头,约翰这样写道: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祂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祂右手拿着七星,从祂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仆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祂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启1:10, 12-18)
就如预言者约翰那样(启1:2),在这段经文中,对于理解教会是见证上帝话语的圣徒团契,我们能得到什么教导?
耶稣基督是活的:荣耀而辉煌地活着,因为满有上帝的生命。祂从死里复活,所以祂既不停滞也不缺席,既不是过去的一部分,也不是活在孤寂和荒僻中:祂乃是威严而自发地临在。而祂的这一临在是交流性的或说启示性的,是以一种完全自由、自发、权威的方式:祂以君王的权能和荣耀,并以绝对的确定性,展现祂自己。祂乃是生命,因此祂就是“临在”。在此没有任何受造物方面的激发因素;祂的自我相交先于人类任何的寻求。约翰听到的“大声音”(启1:10)是在他“身后”,是先于他发出的;约翰“转过身来”(启1:12),朝向那已经向他发出的声音;这声音不是某个受造物的声音,而是“众水的声音”(启1:1);从发声者口中发出的不是人类的言辞,而是上帝审判的“两刃的利剑”。看见并听见这一位,就会被完全地征服:“就仆倒在祂脚前,像死了一样”(启1:17)。但人子并没有杀戮,祂乃是言说。当祂说话时,祂乃是宣告祂自己:“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启1:17-18)祂宣告自己临在于一切的时空,普世性地真实(因为祂无限地活着),向外散布关于祂自己及其充实性的知识。
为什么从这里开始呢?因为约翰描述的正是教会的根本处境——寻求为上帝的话语作见证。教会是人子对其说话的一个聚集。因此,教会言说的处境,并不是被号召来打破沉默,或者采取某种自发性以便与耶稣基督相交。教会言说的处境乃是这样:这一位得胜永活的人子乃是在教会“中间”(启1:13)而不是在她“外围”;并且祂已经在高声说话,将祂自己表明出来。教会言说,因为人子已经向她言说。单单因为有来自这位人子的话语(即单单因为上帝话语的存在),教会才说出话语。因此,教会的这话语就单单是“见证上帝的道”(启1:2)。在教会的话语中,教会并不激活、证明那已被言说的圣言,或为之辩护;她仅仅是在见证那内在清晰、自我呈现的圣言,将那已经在王权中被宣告的内容宣告出来。
那么,这就是圣言在教会中的基本动力;这就是当教会听见圣经中的福音宣告,并且见证她所听之内容时发生的情况。因为耶稣基督在圣经正典中向圣徒团契宣告祂自己。用先知和使徒的话说,耶稣基督将祂自己指示出来(declares himself)。这里的关键因素是耶稣基督位格性的、不可转让的中保行动——祂自己将自己宣告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实。耶稣基督荣耀地坐在天父右边,但祂并没有放下祂自我相交的职分,将其交给圣经文本,从此使这些文本自身自动地成为祂在世上的声音。相反,这位永活者在圣经文本中自己说话:圣经是祂的先知、祂的使徒。圣经是“圣的”,因为它被分别为圣:也就是说,它被上帝分别出来,效力于祂的自我宣告。圣经是被拣选、被分别为圣的辅助者,那位永活者藉着它而在众教会中行走,显明祂的临在。因此,圣经是教会生活中超越性的时刻。圣经不是一本“属于教会”的书,不是某种内在于这共同体之话语实践的东西;教会在圣经中听到的,不是她自己的声音。圣经并不是某些共同意义的贮藏室,也不是一种基督教文化编码,而且假如圣经产生了这些东西,那也不过是因为,圣经是耶稣基督藉着圣灵而喜悦发出“上帝活的声音”(viva vox Dei)的地方。这被上帝分别出来、效力于基督自我显现之目的的圣经,对于教会的生命而言总是侵入性的(从更深的意义上讲,乃是异质性的)。
所有这一切乃是要说,教会聚集围绕于上帝在基督里通过圣灵启示的自我临在,这一临在通过众先知和使徒的著作带到圣徒的团契中。上帝的这一启示是“孤立的”[35],也就是说,它是自生(self-generating)自成(self-completing)的事件。只有上帝知道上帝:这对正确理解教会与圣经的关系至关重要。圣经不应被视为仿佛必须通过教会的接受和解释的行动才能被成全的启示活动要素之一。圣经不是仿佛只有在教会生活中才能完全实现的上帝之相交过程的初始阶段,无论对这种生活的理解是基于传统神学概念还是基于诸如“读者接受”等诠释学概念。圣经以其完美性见证了上帝的启示。正因如此,圣经被认为具有清晰性和充足性的特点。这两种论及圣经的方式都强调圣经的完整性,也就是教会在圣经中遇见那已完全实现的上帝之相交的这一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与“真实临在”这一圣礼概念平行。当然,“真实临在”、圣经的清晰性和充足性,都不会消除受造物的接受式的行动,但它们确实重新调整了受造物的那些行动。因此,当教会“解释”圣经时,它并不是去赋予圣经自身未曾具备的清晰性,也不是去成全启示事件(而圣经仿佛只是这启示事件成全而沉淀的地方)。解释不是澄清或是成全,而是承认,即同意先知和使徒之见证的内在的清晰性和充足性,他们的见证将教会之主的声音带给我们。
上述讨论显然会带来的结果是,关于教会与圣言之关系的某些惯性思维将很大地改变。圣言不是在教会里,而是通过圣经向教会宣告。因此,教会从根本上说不是言说性的而是倾听性的共同体。约翰这位预言者说,他转向那与他说话的声音(启1:12);论到基督徒之聚集的首要动力,几乎没有更简洁的说法了。教会就是那“转向”。而更进一步地说,在这一转向的过程中,恐惧战兢地仆倒在人子脚前的教会,接受了一项特别任务的指派:她被呼召去宣讲。
但她的宣讲有什么特点呢?如果耶稣基督是通过正典文本而显明自己临在的那先知,那么教会的宣讲就是指示或见证基督自己说的话。教会的宣讲乃是第二步(而非第一步)动作,是一种响应行为,其目标在她引人关注她所听见(而非她自己所讲)的内容时得到实现。具体点说,这意味着教会的首要公共语言是解经。解经是试图去聆听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的声音,去聆听“有两刃利剑者的话”(启 2:1、12)。基督徒对圣经的解释既不是文本考古学,也不是诠释学的兴盛,因为正典不是一个堆积了模糊不清的历史数据或宗教意义而需要用解经技巧进行发掘的杂物间。这两种方法都犯了一个错误:将圣经从它在基督与圣灵的相交的计划中的位置上抽离出来,将其自然化。但正确的基督教解经乃是倾听基督通过祂的先知和使徒所发出的话,并试图指明藉着他们的见证所听到的内容。布林格(Bullinger)在他的著作 Decades 中这样说:“对圣经的解释乃是阐明上帝的话语,并为上帝的听众结出许多果实。”[36]他所用的“阐明”一词,一针见血地指明了教会公开宣讲的本质,即它扎根于对圣经宣讲的关注,见证那已向圣徒团契所说的话。“阐明”圣言并不是要试图扩展、启发或改进已经说出的话语,仿佛必须通过教会这边的某些聪明才智,圣言才得以更加显明。相反,所要做的只是让圣言按其所是地呈现,并且因此让自己被置于其支配之下。
因此,我的提议是,作为圣言的有形共同体,教会在她一切言说中都应该以尊崇圣经为特征。这种尊崇的主要表达形式是教会读经的行动,由此她可以为已经宣告的内容作见证。作为一个见证的共同体,恭敬地阅读圣经(聆听并“阐明”耶稣基督的使徒和先知的话语)是教会活动的典范实例。应该补充一点:这种尊崇无法简单地通过圣经权威性的教义得到保证。这一教义是必要的,但不能指望它承担教会在上帝圣言中的生活的全部分量。教会不是仅仅通过正式地肯定圣经的本质(尽管这样的肯定很重要)来证明她是一个圣言共同体,而是要将自己置于圣经之下,以圣经为支配其思想和行动的原则。教会与圣经的关系无法通过关于圣经之权威和默示的神学一劳永逸地解决,而若我们真以为这样能解决问题,我们就是在冒险拦阻那使教会成为教会的运动:朝着教会之主的声音永不停止的转向,以及回应的行动——见证。
三、不是结论的结论
1.福音派基督徒需要一种教会论,他们所需要的教会论是一种福音派的教会论,因为福音是教会性的。但是,这种教会论不是一系列初级本能,抓住任何朝其方向漂去的教义;相反,它必须远胜于此。一种真正的福音的教会论必须位于一系列教义断言的范围内,这些教义断言能够阐明基督教对于上帝、基督、圣灵、拣选、和好、成圣等内容的认信。当今的福音派基督教有时候会试图设想,补救教会论方面固有的漠不关心或极简主义,乃是步入高端的表现。福音派传统近来毫无区别的态度令人担忧,比如她对社会性内在的赎罪理论的态度极为开放,又比如对“关系”这个概念高度热情,将其视为一种神学上的灵丹妙药。但是,在核心不明确的当代教会论共识以外,福音派传统肯定能为大公教会贡献更多的东西。期望福音派传统能稍稍更深入地研究关于恩典的神学,这个期望很过分吗?巴特在梵二会议前后警告罗马天主教,要他们小心,唯恐成为自由派更正教徒;我们或许是不是应该忧虑,唯恐福音派基督徒变成天主教化的更正教徒(即错误地认为,对个人主义和“灵魂自由”的教会论改进的唯一方式,是一种实际上严重消化不良的、关于“完整的基督”的神学)?
2.在目前教会界无法调解的状态中,福音派人士需要把他们从自身传统中领受的东西贡献给更广泛的圣徒团契。当他们面对那些因为认信的缘故分道扬镳的人而做出这些努力时,他们必须不能以一种强硬或焦虑的态度,而要以谦卑的自信和慷慨,专注并受教。然而,只有当福音派人士花时间以所属传统中深入的解经和教义的基础来重新认识自己,这些事情才会发生;更重要的是,只有当福音派人士表现出最高的普遍美德,即承认我们也需要改变,这些事情才会发生。至少,宗教改革传统中的教会应该知道:(宗教)改革的教会,是需要被改革的教会(ecclesia reformanda, quia reformata)。
3.教会论是次要的,圣徒团契的生活才是首要的,因为在这个团契中我们与上帝同在。教会团契的复兴关系到的不是教义,而是对教会的上帝的恳求。“全能的上帝,我们恳求你垂顾你的家人;为了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甘心被卖,被交在恶人手里,并在十字架上受苦以至于死,如今活着,并与你和圣灵,永远的独一上帝,一起掌权,永无穷尽。
作者简介
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是英国圣公会牧师和神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曾经任教于英国杜伦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威克利夫学院、英国牛津大学、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他的著作涵盖了系统神学、历史神学和神学伦理学。
[1] 本文原载于英国《教会论》期刊,2004年第一期,Ecclesiology 1(2004),9-35,承蒙荷兰Brill出版公司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注
[2] Chr. Schwöbel, ‘The Creature of the Word: Recovering the Ecclesiology of the Reformers,’ in C. E. Gunton and D. W. Hardy,eds., On Being the Church: Essays on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Edinburgh: T&T Clark, 1989), 110–55 (120).
[3]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钱曜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0),1031。——译者注
[4] 一种主要在“耶鲁学派”中流行的的教会论,其中掺杂了世俗观念、社会科学的观点或人类学的观点,可以参阅: G. Lindbeck, The Nature of Doctrine (London: SPCK, 1984); idem, The Church in a Postliberal Age (London: SCM Press, 2002), esp. 1–9, 145–65; H. Frei, Typ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5] Paradigmatically, R. Jenson: see Systematic Theology,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7–305; ‘The Church as Communio,’ in C. Braaten and R. Jenson,eds., The Catholicity of the Reforma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1–12; ‘The Church and the Sacraments’, in C. Gunton,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ristian Doctr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7–25. 作为更多背景资料,见重要的文献: D. Yeago, ‘The Church as Polity? The Lutheran Context of Robert W. Jenson’s Ecclesiology,’ in C. Gunton,ed., Trinity, Time and Church: A Response to the Theology of Robert W. Jens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0), 201–37.
[6] Notably R. Hütter, Suffering Divine Things: Theology as Church Practic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0); M. Volf and D. Bass,eds., Practicing Theology: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Christian Lif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1); J. Buckley and D. Yeago,eds., Knowing the Triune God: The Work of the Spirit in the Practices of the Church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1).
[7] H. de Lubac, Catholicism: A Study of Dogma in Relation to the Corporate Destiny of Mankind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1950), 166.
[8] 相关的书籍很多,由多种语言写成,跨圣经神学和历史神学、教义与普世主义学说的范畴。有J.A. Möhler’s 1825 Unity in the Church (ET Washingto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6), 当代基础的文献是:de Lubac’s Catholicism, 绝对那个世纪最经得起考验的教会论文献之一。最透彻的罗马天主教作品是:J. M. R. Tillard, Church of Churches: An Ecclesiology of Communion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1992); 最不妥协的更正教神学家的作品是在:R.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的第二卷中. 有影响力的普及作品:Zizioulas, Being as Communion: Studies in Personhood and the Church (New York: St Vladimir’s Press, 1985) . “梵二”会议的教会论具有核心意义:Lumen Gentium;关于此见:W. Kasper, ‘The Church as Communion: Reflections on the Guiding Ecclesiological Idea of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Theology and Church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148–65.关于普世主义的资料,见报道:S. Wood, ‘Ecclesial Koinonia in Ecumenical Dialogues,’ One in Christ 30 (1994), 124–45; H. Schülte, Die Kirche im ökumenischen Verständnis (Paderborn: Bonifacius, 1991); G. R. Evans, The Church and the Churches: Toward an Ecumenical Eccles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91–314, 特别是:N. Sagovsky, Ecumenism, Christian Origins and the Practice of Comm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更宽泛的见:J. Hamer, The Church Is a Communion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64); D. M. Doyle, Communion Ecclesiology: Vision and Versions (Maryknoll, NY: Orbis, 2000); Chr. Schwöbel, ‘Kirche als Communio’, in idem, Gott in Beziehung. Studien zur Dogmatik (Tübingen: Mohr, 2002), 379–435.
[9] J. M. R. Tillard, Church of Churches: The Ecclesiology of Communion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1992), 319; original emphasis.
[10] de Lubac, Catholicism, 28
[11] H. de Lubac, Surnaturel (Paris: Aubier, 1946). 这里有用的背景资料是:F. Kerr, After Aquinas: Versions of Thomism (Oxford: Blackwell, 2002), 134–48.
[12] 天主教的一个运动。——编者注
[13] Authoritatively in Lumen Gentium ,39–42.
[14] K. Barth, The Theology of the Reformed Confessions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2002), 142.
[15]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V.i.3 ,1015.
[16]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II.xi.10, 737. 关于加尔文就在基督里“非实质的参与”的教义,见近期的作品:J. Canliss, ‘Calvin, Osiander and Participation in G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Theology 6 (2004), 169–84.
[17]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II.xi.10, 737.
[18]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II.xi.10,737.
[19]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II.xi.10,737.
[20]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V.i.1,1015. 更多关于此问题见:G. C. Berkouwer, The Church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6), 77–102.
[21] Jenson, ‘The Church as Communio,’ 3.
[22] A. M. Ramsey, The Gospel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36), 6.
[23] Ramsey, The Gospel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35–36.
[24]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V.vi.10,1110.
[25] de Lubac, Catholicism, 8.
[26] Barth, The Theology of the Reformed Confessions, 80.
[27] D. Bonhoeffer, Discipleship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1), 225.
[28] 当代最新的关于此的表达见O. Tjørhom, Visible Church – Visible Unity: Ecumenical Ecclesiology and ‘The Great Tradition of the Church’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2004). 关于普世运动见M. Tanner, ‘The Goal of Unity in Theological Dialogues involving Anglicans,’ in G. Gassmann and P. Nørgaard-Højen,eds., Einheit der Kirche (Frankfurt A/M: Lembeck, 1988), 69–78; ‘The Ecumenical Future,’ in S. W. Sykes et al. ,eds., The Study of Anglicanism (London: SPCK, 1998), 427–46; M. Root, ‘ “Reconciled Diversity” and the Visible Church’, in C. Podmore ,ed., Community – Unity – Communion (London: Church House Publishing, 1998), 237–51; J. Webster, ‘The Goals of Ecumenism,’ in P. Avis,ed., Paths to Unity: Explorations in Ecumenical Method (London: Church House Publishing, 2004), 1–12.早期著作可以参考出色的论文,M. Thurian, ‘Visible Unity of Christians,’ Visible Unity and Tradition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4), 1–49.
[29] 见K.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1 (Edinburgh: T&T Clark, 1956), 656–58; IV/2, 619; IV/3, 726.
[30] Yeago, ‘The Church as Polity?’, 229.
[31]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V.i.3 ,1015.
[32]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V.i.3,1015.
[33] 教会论首要是见证贯穿在巴特的《教义》第四卷中。更多见:Chr. Schwöbel, ‘Kirche als Communio’ and ‘The Creature of the Word’.另见:T. F. Torrance’s deploy-ment of the somewhat similar notion of ‘hypodeigma’, in Royal Priesthood: A Theology of Ordained Ministry (Edinburgh: T&T Clark, 1993), 94–97, 尽管托伦斯关注了更多上帝与人类行动之间的延续性,超过我在这里所建议的。
[34] K. Barth, ‘The Christian as Witness’, God in Action (Edinburgh: T&T Clark, 1936), 107.
[35] 这是巴特的话, 出自他的著作The Theology of the Reformed Confessions, 48–49, 56.
[36] H. Bullinger, Decades I and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49), 72.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