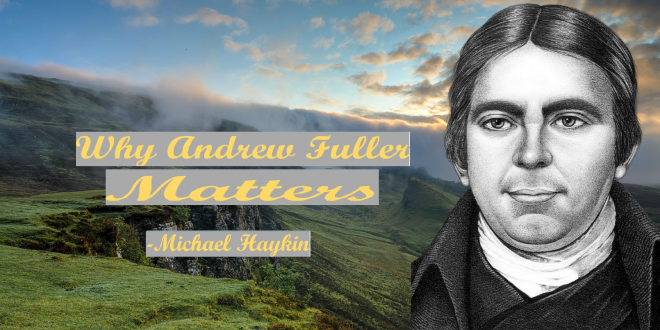文/迈克尔·海金(Michael A. G. Haykin) 译/穆桑 校/榉木
引言
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在为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撰写的那本权威传记里指出,这位伟大的废奴主义者平生最为深刻的喜乐,是他享有的友谊,他以此为准则——“绝不放过任何一次与善良或优秀的人结识的机会”。[2]正如他的几个儿子后来所言,这意味着他家里“没有客人登门的时候是很少见的”,有的客人来得很早,赶得上与威伯福斯一起吃早餐,所有的客人加在一起,为威伯福斯卓越的交际技巧提供了用武之地。[3]威伯福斯在家里接待的客人中,就有浸信会神学家安德鲁·富勒(Andrew Fuller,1754–1815),威伯福斯极为敬佩他的神学才能。[4]有一次,富勒到访的消息被通报后,威伯福斯竭力尽快将他介绍给他的一个儿子。“你知道安德鲁·富勒吗?”他问道。“不知道,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答复如是。“啊,你一定要认识他,”威伯福斯说,“他是个卓越的人,因为天赋出众而从低微的境况中脱颖而出。”
富勒进来了,如威伯福斯后来记述这位浸信会作家的造访时所言,“他是一个心智超群的人”,但带有“非常明显的田园生活的印记(vestigia ruris)”,因为他看起来“活脱一名铁匠”。[5]威伯福斯的描述符合事实,富勒除了基本的读写训练,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然而他的天赋与上帝的恩典使他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浸信会)神学家”,如司布真所言。[6]
正是富勒笔下的著作,使得威伯福斯与司布真给出如此盛赞。比如,那本巧妙驳斥自然神论的著作,那本完美表述启蒙运动关于上帝的思想的著作,或者那本依照圣经里的坚实证据对当时的极端加尔文主义做出回应的著作。纵观十八世纪,极端加尔文主义在毁坏不少英国浸信会团体的事上发挥了作用[7],进而导致富勒作为之后被称为浸信会传道会(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干事广泛参与各项事务。该传道会最著名的宣教士,是富勒的一位好友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1761–1834)。事实上,如宣教学家哈里·布尔(Harry R. Boer)所言,“富勒坚持认为,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有责任相信福音”,他在批驳极端加尔文主义的著作中宣布的这个立场,“在克理的宣教异象得以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8]
不过有人会说,我们并没有生活在18世纪,我们的争战不是针对自然神论的极端理性主义或极端加尔文主义的近乎宿命论视角之类的错谬。那么,为什么要读安德鲁·富勒?下文之中,我要列明安德鲁·富勒的生命与思想对今天的我们依然重要的四个原因——一句话,安德鲁·富勒何以意义重大。
一、从富勒的归信得到的教训
罗伯特·富勒(Robert Fuller,1723–1781)及其妻子菲利帕·甘顿(Philippa Gunton,1726–1816),相继租了几个牛奶场经营。[9]他们的儿子安德鲁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1754年2月6日出生于威肯,剑桥郡一座农业为主的小村庄。富勒七岁时,父母移居到距离威肯两英里半的索厄姆(Soham)村。刚在索厄姆安顿下来,他们就加入了当地的加尔文宗浸信会。这间浸信会教会的牧师名叫约翰·伊夫(John Eve),是一位极端加尔文主义者,或者如富勒所言,是教导中“含有错误的加尔文主义”的一个人。[10]许多年以后富勒回忆起来,说伊夫的讲道“不宜于唤醒良知”,“对未归信的人几无所言或一无所言”。[11]因此,虽然事实上富勒常常到浸信会的礼拜堂参加聚会,可他对所听的道几乎没有思想或留心。
不过富勒到了十四岁时,开始思想生命的意义与目的。然而事实显明,他自小耳濡目染的极端加尔文主义,是他归向基督的真正障碍。极端加尔文主义认为,为了逃往基督得救恩,一个人必须有依据相信他是被基督悦纳的,而这一“依据”是主观性的——1)相信自己是有罪的,2)这种相信导致的后果:心里感到痛苦——这两点被大多数极端加尔文主义者视作依据。按照这一观点,这些经历是一个标志,表明上帝正在改变经历到这些的个人。这种归信观直接来自一个论点:圣经只邀请那些觉知自身之罪的罪人来信基督。这一教导的最终后果,不是将归信与信心的本质置于“相信福音”,而是置于“劝我们关注福音的益处”;非但没有将被定罪之罪人的注意力从自身引向基督,反倒使之向内关注自身,去搜寻自己正被归正的证据。[12]不过富勒最终决定:“我要将我的灵魂,我的有罪、失丧的灵魂交到祂的手中——如果我会灭亡,那就灭亡吧!”于是,在1769年11月,富勒与上帝和好,困苦的灵魂在钉十字架的基督里面得以安息。[13]
他归信前与归信中的个人经历,最终教他懂得了三件事,尤其是关于归信的。第一,认为唯有那些觉知自身光景并为之苦恼的人才有依据或权利投奔基督,这是错误的。富勒反对这种观点,并提出自己的主张:福音劝世人相信基督,这是投奔主耶稣的充足依据。第二,真正的信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不是向内关注自身,以确定自己是否有认识基督、拥抱救恩的愿望。第三,富勒认识到,真正的归信植根于心的喜好的彻底转变,彰显于以荣耀上帝为目的的生活方式。[14]这些对真归信之本质的洞见,在今天仍然意义重大。
二、了解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责任
归信后的那个春天,即1770年春天,富勒受洗,加入索厄姆教会。不过那年晚些时候,该教会因为“有罪的男人和女人是否有能力……遵行上帝的旨意,保守自己不犯罪”这个问题而分裂,令人痛心。索厄姆教会因为这个议题而产生的纷争——富勒后来称之为“我少年时期的苦艾与苦胆”[15]——最终导致伊夫牧师于1771年10月辞职而去。富勒后来谈到,虽然这次纷争令他深感痛苦,可最终他是由此而得蒙引导,进入了“那些对于神圣真理的认识”,那些认识后来体现于他出版的几本重要著作当中。
1774年1月,教会邀请他定期登台讲道。16个月后,富勒被按立为索厄姆教会的第二任牧师。这间浸信会由47名成员组成,聚在租来的谷仓里敬拜。直到1783年,也就是富勒蒙召到了北安普敦郡的凯特林浸信会的一年后,该教会才有财力建设了一处更加固定的场所。
服事的第一年,富勒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与研究。他只听过伊夫的讲道这一种教导模式,因此也像伊夫一样讲道,拒绝敦促未归信者归向基督。但是他对极端加尔文主义的推论越来越不满。他开始发觉,他的“讲道是反圣经的,在许多方面是有缺陷的”,但是他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他觉得自己必须慢慢摸索着“走出迷宫”。[16]
与此同时,富勒也沉浸在两位浸信会作家的著作当中: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上世纪著名的福音布道家;约翰·吉尔(John Gill,1697–1771),18世纪特别浸信会(Particular Baptist)神学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富勒发现,吉尔的系统神学中有很多内容都是有益的,但因为吉尔与班扬的明显区别而深受困扰。二人都是热切的加尔文主义者,但班扬所主张的,是救恩一视同仁地白白提供给罪人,吉尔却不这么主张。起初富勒得出了错误结论:虽然班扬是“伟大而敬虔的人”,可他对福音的认识不像吉尔那么清晰。不过,当他研读十六、十七世纪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清教徒神学家约翰·欧文(John Owen,1616–1683)的作品时,发现他们也“探讨……对罪人发出的投奔基督得救恩的白白邀请”。换句话说,他发现,就传道来说,不仅是吉尔与班扬之间有明显区别,十六、十七世纪的加尔文主义与十八世纪早期的加尔文主义之间的区别更大。
为了帮助解决自己关于极端加尔文主义的疑问,富勒开始撰写一篇论文,后来命名为“十分可佩服的福音”(The Gospel Worthy of All Acceptation),用于指引自己。初稿写就于1778年,大致的终稿完成于1781年。该作品的两版均于富勒生前出版。第一版于1785年在北安普敦出版,副标题为“人有义务完全相信并真诚赞同上帝启示的一切,其中涉及相信基督的本质,以及有福音临到之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责任”(The Obligations of Men Fully to Credit, and Cordially to Approve,Whatever God Makes Known,Wherein is Considered the Nature of Faith in Christ,and the Duty of Those where the Gospel Comes in that Matter)。第二版于1801年面世,副标题较为简单,“罪人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责任”(The Duty of Sinners to Believe in Jesus Christ),充分表达了该作品总的主题。富勒坦白承认,第一版与第二版(1801)之间有重大区别,主要关乎特定救赎教义。不过这部作品的主题未变:所有听到或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都有责任相信基督。
这部划时代的作品旨在忠于古旧加尔文主义(historic Calvinism)的核心要点,与此同时,除了将悔改与归信这一普世责任给听众讲透之外,竭力不给传道人任何选项。1783年,富勒从索厄姆移居北安普敦郡,撰写了一篇文章,在凯特灵市(Kettering)浸信会就任牧职的仪式上申明信仰。在那篇文章中,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我相信,向所有将要听到福音的人,清晰而忠实地将福音传讲出来,是基督的每一位传道者的责任……爱主耶稣基督,信靠祂而得救恩,是他们(即听众)的责任……因此我相信,向他们发出自由而庄严的演讲、邀请、呼唤和警告,不仅是一致的,而且是直接适宜的,是在上帝之灵手中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的途径。我认为这是我的一部分责任,如若疏忽,于灵魂的灭亡就难辞其咎了。[17]
早前的这些年间,富勒抱持严格的圣经主义,在他探索真理的方法中,这是至为关键的因素。如富勒的好友约翰·瑞兰德(John Ryland. Jr.,1753–1825)在追忆他的文中所写:“他从人与书得到的帮助,要少于从别的地方得到的帮助;但他义无反顾地思想圣经、用圣经祷告、研究圣经,从而打下了稳固的根基。”[18]1780年,富勒写下与自己的立约,谈到他“决心不遵行任何二手原则,只从(上帝)话语这纯粹的源泉搜寻一切”。[19]富勒从不惮于回到圣经,基于上帝无误的话语,质疑一切被承继为正统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富勒不向其他基督徒作家学习。我们谈过他读约翰·班扬、约翰·欧文、约翰·吉尔。从很多方面看,美国神学家约拿单·爱德华滋是他的神学导师。但是对所有这些人的思考,都要接受无误之圣经的检验。
《十分可佩服的福音》让富勒卷入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当中。这部作品出版之后不久,伦敦的两位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威廉·巴顿(William Button,1754–1821)与约翰·马丁(John Martin,1741–1820)刊文攻击富勒。值得注意的是,二人虽然攻击富勒,可后来都与富勒交好。举例来说,巴顿自“浸信会传道会”成立初期直到自己去世,一直是该机构的坚定支持者。1797年,马丁还谈到对富勒的衷心敬佩。富勒执笔回应这两位浸信会牧师中的前者时,发现自己遭到另一方的攻击,来自神学光谱另一端的代表,即一般(即亚米念派)浸信会人士丹·泰勒(Dan Taylor,1738–1816)。
后来,富勒会将自己的神学立场(有人称之为“富勒主义”[Fullerism])称为“严格加尔文主义”(strict Calvinism)。他试图将之与极端加尔文主义区别开来,后者“比加尔文还要加尔文主义”,“近乎反律主义”;也试图将之与温和加尔文主义区别开来,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1615–1691)实质上就是持这种神学观点,而富勒认为温和加尔文主义是“半亚米念主义”(half Arminian)。在富勒看来,严格加尔文主义就是“加尔文的体系”。富勒的神学(今天有人称之为“福音派加尔文主义”[evangelical Calvinism]),是他的好友威廉·克理的神学,也是他后来的崇敬者司布真的神学。这种神学能够将两点结合起来:一是对罪人的得救抱有强烈的热心,二是抱着对上帝主权的极大信心,以传道拓展上帝的国度。
三、从富勒参与的其他辩论得到的教训
富勒在这次辩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参与其他重要领域的神学辩论。1793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全面批驳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1733–1804)的苏西尼主义(Socinianism)——《就道德倾向考察与比较加尔文主义体系与苏西尼主义体系》(The Calvinistic and Socinian Systems examined and Compared,as to their Moral Tendency)。由于普利斯特里的大力鼓吹,否定三位一体和基督神性的苏西尼主义或神体一位论,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中,成为英国不从国教者当中最主要的一种异端。富勒对苏西尼主义的反驳,充分表明了18世纪浸信会思想以基督为中心的特质。富勒以妙笔指出,早期教会以基督位格神性的尊贵与荣耀为主题,他称之为“他们心爱的主题”。
之后,在1800年,富勒出版了《福音即福音的见证》(The Gospel Its Own Witness),这本书是18世纪对自然神论,尤其是对小册子作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所主张的自然神论,所发出的最具权威的浸信会视角的回应。这部作品是富勒最受欢迎的书之一,1802年前出了三版,接下来的三十年又重印了好几次。威伯福斯认为,这是富勒所有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这部作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中,富勒比较和对比了基督信仰与自然神论的道德影响;第二部分旨在藉由圣经各卷的总体一致性表明基督信仰的神圣来源。
富勒参与的另一次意义重大的辩论,是针对桑德曼派(the Sandemanians),即罗伯特·桑德曼(Robert Sandeman,1718–1771)的追随者,他们大多数人持唯理智主义者式的信心观,从而将自己与18世纪别的福音派区别开来。使人得救的信心,即“对纯粹事实的纯粹相信”,他们因这一基本神学信条而闻名。桑德曼真心想要高举上帝救恩的绝对无偿,于是试图抹杀人的理性、意志或意愿在使人得救的信心上的任何印记。富勒在《严厉批判桑德曼主义》(Strictures on Sandemanianism[1810])中讲了两个要点。第一,如果信心仅仅关乎理智,那就无从分别真基督教与挂名基督教。挂名基督徒思想上也认同基督教的真理,但那些真理并没有掌管他的心,重塑他的情感。因此,第二,关于基督的知识,是独特的一类知识。举例来说,认识祂,不仅关涉知道关于祂的某些事情,比如祂由童女所生这个事实或者祂钉十字架的一些细节,而且关涉与祂团契的热望,因祂同在的甜蜜而生的喜乐。
这三次辩论,每一次都可以追溯至启蒙运动之理性主义的影响。富勒在这三次辩论中表明,自己是与当时文化所表达的世界观有密切接触的牧师—神学家。有例为证,富勒并没有将精力主要花在17世纪清教徒前辈所从事的争战,即关于教会问题的斗争。如果说富勒就捍卫基督教真理这件事对我们有所教导的话,那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特定处境中基督教所面临的挑战必须保持警觉。
四、从富勒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敬虔观得引导
最后,在我们这样一个教会内外的人都对灵性着迷的年代,富勒的敬虔观可以教我们很多。举例来说,他深信,基督的十字架位于基督信仰的中心。1802年,富勒断言,十字架是“福音真理的所有线条得以交汇并联结的中心点”。正如太阳对于太阳系的维系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同理,“十字架的教义之于福音的体系,前者是后者的生命。”[20]十二年后,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富勒直接宣称,基督的代赎之死就是“福音体系的生命之血”。[21]从另一个角度看,传讲和教导钉十字架的基督,可以比作“金环,握在手中就可以将福音真理的整条链子牵动”。[22]总之,十字架是“基督教恢弘的独特之处与首要的荣耀所在”,几乎等同于福音本身:“由基督的血而得救赎的教义……因其显赫地位而被称为福音”。[23]
如果这样看待基督的死,那当我们发现富勒断言:历世历代,上帝喜悦尊荣的一直是十字架的教义,就无需惊讶了。无论什么地方,在教会享有的灵性火热、高涨的时期——如富勒给出的称呼:“大复兴时期”——基督的救赎之工总是占据高位。富勒指出,位于改教运动的中心,由改教家赋予突出地位的,正是这则教义。对于清教徒与富勒的属灵前辈——十七世纪以及十八世纪早期的不从国教者来说,这是居于首位的主题。[24]在富勒的年代,摩拉维亚宣教士在西印度群岛,在爱斯基摩人中间,尤其是在格陵兰岛大获成功,他们宣教的胜利一直是十字架的胜利:“因基督之死而得救赎的教义……构成他们服事的伟大主题。”[25]
因此,如果一间教会或一个宗派拒绝十字架的教义,就比富勒不客气地说起的“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一团东西”好不了多少。去掉基督的救赎之工,“旧约的全部仪式之于我们,不比死气沉沉、乏味不堪的一团东西之于我们意义更多:预言失去了引人关注的、让人喜爱的一切;福音被废除,或者对于失丧的罪人不再是自身宣称的好消息;实践性宗教被剥夺了最强大的动力,福音的落实被剥夺了独特的荣耀,天堂本身被剥夺了最强烈的喜乐。”[26]举例来说,为什么在富勒那个时代国教教区教会的出席率低得那么可怜?对富勒来说,答案显而易见:大多数神职人员不传讲十字架的教义……他们所讲的道中,没有什么东西使会众的心灵生发兴趣,没有什么东西抵达会众的良知。[27]因此,对十字架的理解,是真正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与挂名基督教之间的主要分界线。
我们可能因为接受教育而成为基督徒,可能精通基督教这门学科,可能能够沟通、传讲、写作以捍卫基督教,但是如果钉十字架的基督之于我们,不像美食之于饥饿的人,清泉之于干渴的人,我们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我们在其他主题上犯错,虽然生命会受亏损却仍然可能存活;但在这个主题上犯错,就是在要害部位染病,通常的后果就是死。[28]
正由于此,当1796年,苏西尼派思想对英国不从国教者的队伍构成巨大威胁时,这位浸信会牧师在自己所写的一封信中宣称,凡是不依靠祂的挽回祭以求上帝悦纳的,他不能视之为同道信徒。[29]
对基督的死所成就的福分的反思,在富勒的作品中比比皆是。比如,他坚持认为,十字架是罪人得与圣洁上帝和好的唯一道路。1798年,有人请富勒简要记述他早年的属灵历程,富勒指出,他在归信之时就得以确信:“上帝遣我下地狱,也是完全公义的,我必须下地狱,除非藉由纯粹的恩典而得救。”他接着解释说,“纯粹的恩典”要求我们摈弃“一切错误的信心”,唯独信靠基督的死而得救。在另一个场合,他也写道: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是“失丧世界的唯一盼望,是得蒙上帝悦纳的唯一媒介,是我们就近祂面前时唯一可被接受的理由”。[30]
而且,这位浸信会牧师从不厌倦如此强调:要脱离内住之罪的污染,得内在的平安与心灵的洁净,方法只有一个,经验性地认识钉十字架的基督。富勒在评述基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的时候说:“耶稣的血”是“向罪与不洁敞开的泉源”。[31]信徒能得圣灵住在自己里面,根基也只有一个:基督的死。[32]不仅如此,也是在十字架上,“黑暗的权势被剥得精光”,撒但“被女人的后裔击败,其计谋遭到全宇宙的嘲笑”。[33]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之间的和睦是用祂的血为代价买来的”,在对十字架的教义有共识的地方,“人们会在无关紧要的事上彼此宽容且互相忍让”。[34]
也有必要指出,富勒有几次病得厉害,认为自己到了死亡边缘,这时他提醒朋友们,他所持的盼望只有一个根基,那就是耶稣替他死。1801年秋,他的病情严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几乎不间断的咳嗽”与“几乎不间断的发烧”,这时他写信给好友约翰·萨克利夫(John Sutcliff,1752–1814),说他面对可能到来的死亡,是平静的。
我的心平静而且相当喜乐。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参提后1:12)。就我所站的根基来说,我一无所虑;想到自己时,我满心忧虑,我是可怜而污秽的受造物,是无用的仆人。我的盼望不在别处,唯在来拯救罪魁的那位救主。[35]
11年后,他再次病重时,对萨克利夫说:“我别无他法,只有以救主的死为根基的对永生的坚定盼望。”[36]1815年,他确实即将离世时,在写给另外一位好友约翰·瑞兰德的最后一封信中也有类似的情感流露,正如在写给萨克利夫的那两封信中所表达的。引用了提摩太后书1:12的一部分之后,富勒接着说:
我是可怜而有罪的受造物,但基督是大能的救主。我讲道、写作,有很多内容是在批驳对恩典教义的滥用,但恩典教义是我的全部救恩、全部渴望。除了惟独从救恩而来的盼望,我没有别的盼望,而这救恩是透过我的救主的代赎,藉由纯粹出自上帝主权的、有效的恩典造就的。有了这份盼望,我就可以从容地步入永恒。[37]
作者简介:
迈克尔·海金(Michael A. G. HayKin),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1982年于多伦多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教会史教授。
[1] 本文译自Michael A. G. Haykin, “Why Andrew Fuller Matters,” in The Evangelical Quarterly (Leiden:Brill, 2020), 26 Apr, 2020, Vol.91, Issue2, 163–72。这篇论文是作者该文章的英文版,原文为:“Le precieux heritage d Andrew Fuller,” in Jesus Batira Son Eglise:Un Hommage a Jacques Aiexanian(Montreal, QC:Editions Cruciforme, 2013), 157–71。正文略有编辑,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William Hague, William Wilberforce:The Life of the Great Anti-Slave Trade Campaigner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7), 506.
[3] Robert Isaac Wilberforce and Samuel Wilberforce, The Lif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London:John Murray, 1839), III, 388.
[4] Wilberforce and Wilberforce, Lif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III, 389.
[5] Wilberforce and Wilberforce, Lif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III, 389. 黑格并未提及威伯福斯与富勒的友谊。更加异常的是,黑格对富勒的好友威廉·克里也只字未提。尤其是考虑到黑格投入很大的篇幅来讲威伯福斯为在印度服事的英国宣教士争取自由方面发挥的作用时,这一点实属异常。
[6] 转引自Gilbert Laws, Andrew Fuller:Pastor, Theologian, Ropeholder (London:Carey Press,1942), 127。
[7] 富勒对自然神论的回应,见The Gospel Its Own Witness(1800);他对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回应,见The Gospel Worthy of All Acceptation(1785 [1st ed.];1801 [2nd ed.] )。
[8] Harry R. Boer, Pentecost and Missions (Grand Rapids:Wm. B. Eerdmans Publ. Co., 1961), 24.
[9] Andrew Gunton Fuller, “Memoir,”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Joseph Belcher修订(1845 edn;repr. Harrisonburg, VA:Sprinkle Publications,1988),Ⅰ,1.富勒家人的具体情况,见Andrew Gunton Fuller, Andrew Fuller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 1882), 11–12。
[10] Fuller, “Memoir,” I, 2,12.
[11] Fuller, “Memoir,” I, 2.
[12] Andrew Fuller, Strictures on Sandemanianism, 见于Twelve Letters to a Friend,收录于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I, 563–564。也见于E. F. Clipsham, “Andrew Fuller and Fullerism:A Study in Evangelical Calvinism,” The Baptist Quarterly 20(1963–1964), 99–114(103)。
[13] Fuller, “Memoir,” I, 2.
[14] Clipsham, “Andrew Fuller and Fullerism,” 106–07.
[15] Fuller, “Memoir,” Works, I, 10。富勒对这次争论的描述,见 “Memoir,”, I, 8–10。
[16] Fuller, “Memoir,” I, 13.
[17] 转引自A. C. Underwood,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aptists (London:Carey Kingsgate Press Ltd., 1956), 163–64。
[18] The Work of Faith,the Labour of Love,and the Patience of Hope,illustrated;in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London:Button & Son, 1818), 43.
[19] Life and Death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129.
[20] The Calvinistic and Socinian Systems examined and Compared, as to their Moral Tendency, in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I, 182.
[21] Letters on Systematic Divinity, in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 687.
[22] The Common Salvation,in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 411.
[23] Calvinistic and Socinian Systems, in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I, 181; The Believer’s Review of His State, in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 303.
[24] God’s Approbation of our Labours, in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 190; The Common Salvation, I, 412; Calvinistic and Socinian Systems, II, 121; Decline of the Dissenting Interest, in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II, 486.
[25] Calvinistic and Socinian Systems,II, 128.
[26] Christian Steadfastness, in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 527; Calvinistic and Socinian Systems, II, 191-92.
[27] Decline of the Dissenting Interest, III, 487.
[28] Letters on Systematic Divinity, I, 691。
[29] Agreement in Sentiment the Bond of Christian Union, in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II, 490.
[30] Truth the Object of Angelical Research,in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 665.
[31] Christ Washing the Disciples’ Feet, in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 657。
[32] The Future Perfection of the Church, in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 251–52; The Gospel Its Own Witness, in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I, 82–83, footnote。
[33] Truth the Object of Angelical Research, in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 665.
[34] A Peaceful Disposition, in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I, 538; Letter to Christopher Anderson, 26 March, 1805(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s, Angus Library, Regent’s Park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35] Letter to John Sutcliff, September 1, 1801 ( Letters of Andrew Fuller, typescript transcript, Angus Library, Regent’s Park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36] Letter to John Sutcliff, May 31,1812(Letters of Andrew Fuller).
[37] 转引自Ryland, Life and Death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355。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