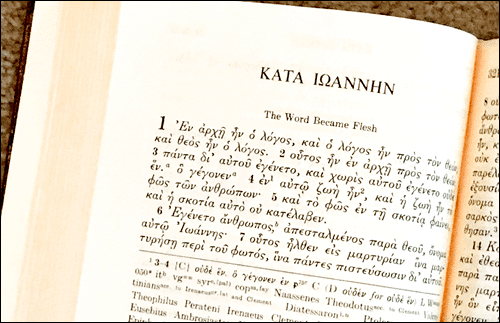文/蒋虹嘉 译/简思茗
“正典”(canon)意指一种度量标尺,而在宗教的语境下,“正典”指的则是一种信仰准则。有关新约正典的问题对基督教神学家来说并不是新事物。然而,过去几十年中,在这一话题上涌现出了许多由所谓的圣经学者撰写的、供非专业人士阅读的著作。[1]这些著作借着挑战新约圣经的权威性,来试图影响普通基督徒的认信。这些圣经学者们所主张的观点之一便是:新约正典是直到四世纪才出现的。[2]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只是出现的时间,而是对正典的定义,以及用什么样的框架来鉴定正典。
在本文中,笔者首先将陈述这种“四世纪出现说”的观点,包括该观点对正典的定义、主要论据、结论以及影响。随后,笔者将讨论改革宗信仰的立场,即:新约正典在一世纪,当二十七本经卷作为神所默示的话语被赐给教会之时,就已经存在了。笔者会基于对正典的定义,从“启示”的角度和救赎历史的框架加以论证。
对“四世纪出现说”的看法
首先,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正典是如何被定义的。A.C.桑德伯格(A. C. Sundberg)是持这种“四世纪出现说”的主要学者之一,按照他的说法,正典是指含有二十七经卷的最终固定列单。[3]换言之,只有等到“确定正典经卷不容更改的列单”这一过程最终完成,正典才产生出来。虽然这些经卷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也要等到教会就正典经卷的最终列单达成共识,这些经卷才能被算为属于正典。
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至少有三个。第一个论据是:正典性并不是指某卷书的内在本质,而是解经的人对该卷书所赋予的特别“地位”。[4]从这一意义来说,所有经卷最初都是“平起平坐”的,没有一卷书是作为圣经的一部分来被撰写的。[5]第二个论据是:在公元一到四世纪,教会面临着独特的宗教、社会文化、政治环境。教会与诸如马吉安派(Marcion)、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孟他努主义(Montanism)等异端邪说争战;[6]要向社会表述教会的身份;[7]为要在诸多的基督教派别中“稳操胜券”,教会发展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8]教会还要应付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基督徒受迫害、书籍被焚烧这样的状况。[9]在这种局面下,教会需要建立一个正典来满足上述的多重功能。第三个论据是:由于正典的确定是一个彻底由人来完成的过程,那么教会所扮演的角色就必须是决定性的。[10]在建立正典的过程中,正是教会在对这些经卷进行筛选。
要讨论这些论据,一种比较有意义的做法,便是追溯一下教会历史,来明确教会在“确定正典”这件事上,完全达成共识所涉及的具体事件及时间。事实上,直到十六世纪的天特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这种正式的教会行动才出现。[11]然而,到二世纪末,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希伯来书除外),以及彼得前书和约翰一书已被广泛接受为正典经卷;[12]对其他经卷的争论又持续了两个世纪。初代教会用于评估正典的标准(并非每条都是平等的)包括[13]:1)使徒性——该经卷是由某位使徒撰写的;2)正统性——该经卷符合信仰准则;3)远古性——该经卷是在使徒时期撰写的;4)使用程度——该经卷被东西方教会普遍使用。到四世纪末,通过教会的种种裁决,形成了二十七卷正典经卷的最终列单。由此,现代的学者们便得出结论:新约正典是在四世纪出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有几点重要涵意。首先,如果新约正典纯粹是人为过程的产物,那么其权威性就仅仅来自于人的裁决,而非来自于神,这意味着否定了新约经卷的神圣权柄(divine authority)。基督徒顺服正典作为其信仰和生活的准则,这必须以圣经的神圣起源(divine origin)为基础。如果这个基础被除去,正典也就变得像人写的书一样,无权宣称对基督徒信仰和生活有着绝对的权柄。
其次,如果正典是教会造出来的,就意味着教会不仅握有高于正典的权柄,而且这种权柄还是绝对无误的。但哪里能找到“教会无误”的依据呢?教会是容易犯错误的,就像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那样。因此,如果正典要依赖于教会,我们便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正典的无误性。
再次,与上述担忧相关的是,这一观点还会产生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拥有的正典是“留有余地”(仍未完全),还是“不容更改”(已经完整)?如果现在又发现了某一古卷,其内容相似于或者符合逻辑地延展了正典里的那些经卷,这又当如何处理呢?另外,如果有证据表明这一经卷符合正典性的四大标准(使徒性、正统性、远古性、普遍使用),那么教会是不是应当聚集起来对该经卷评估一番,将其也列入正典,从而使正典更为完整?
总而言之,正典“四世纪出现说”的观点呈现了几个根本性的缺陷:1)通过将正典的概念局限在确定正典的最终阶段,将正典与圣经分割开来;2)通过将这些正典经卷视为不过是属人的产物,将神圣起源与人类中介(human agency)混淆起来;3)未能将正典的客观存在与教会对正典的主观接受区分开来。
改革宗信仰的立场
对比上述观点,改革宗信仰认为,新约正典出现于这些正典经卷成书的公元一世纪。这是根据正典的本体论定义(the ontological definition of canon)[14],是基于这些经卷最初被上帝所默示出来,而不是基于这些经卷最终如何被教会接受或使用;是基于这些经卷本身是什么性质的书,而不是基于它们的功能。这一本体论确定方式与《威斯敏斯特信条》是一致的:强调神的默示(divine inspiration)是圣经正典自身特有的特征(1.3),圣经正典之所以是权威,乃是因为神是其作者(1.4)。这些经卷的正典性存在于这些经卷的自身当中——这是一种内在的特性。
首先,我们要思考一下神圣起源。正如圣经所宣称的那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即:由圣灵“所呼出的(breathing out)”(参提后3:16)。在人类作者“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1:21)这件事上,圣经既谈到了神圣起源也谈到了人类媒介(human instrumentality)。当中的主动权和所产生的果效都是来自圣灵,而非来自人类中介(human agent)。圣经是属神的产物,而非人的产物,也不是神与人的混合产物。圣经是“神活泼的声音,全方位地直接言说于读者。”[15]
其次,因着圣经的神圣起源,我们应当在圣经的客观权威与教会或个人的主观接受之间做出区分。加尔文提到,圣经是自证为真,不受制于人的证明或推理。[16]除了圣灵在人心中作见证,无人能够彻底被说服,从而承认圣经的无误性和属神权柄。[17]从历史的角度看,教会不过是认识到了圣经已然存在的权威性。这种认知过程本身就见证了圣经“自证为真”这一特征。考虑到这二十七经卷在人类作者、撰写年代及地点上是有差异的,我们有理由预期,在某经卷的成书及其被教会所接受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耽延。这甚至会导致出现一些对于个别经卷的分歧和争议。克鲁格(Michael Kruger)却提醒我们:“尽管有这些分歧,我们依然可以确信,教会就这二十七经卷所达成的最终共识,可靠地表明了这些经卷的正典性。”[18]
再次,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圣经的作者是神,神向我们启示了祂对人类救赎的整个图景,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正典是已经完整、“不容更改的”(closed cannon)。正如克鲁格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讲,正典根源于救赎史。”[19]从救赎历史的角度看,新约并不是独自存在的,而是与旧约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神在旧约里救赎行动的模式——先是救赎事件、紧接着是话语解释(例如:出埃及记)——必然预示着会有新的话语启示从神而来,用以解释神在基督里的最终救赎之工。此外,旧约是伴随着旧的圣约(the old covenant)所写成的文本,与古代近东宗主权条约的写作结构一致。随着末世的到来,初代基督徒相信自己已从神那里领受了新的圣约(the new covenant),因此,他们期盼这个新的圣约也能有书写文本。随着上帝的救赎在作为新圣约之中保的基督身上完成,客观启示也结束了,新约也由此完成了。我们便拥有了已经完整、“不容更改”的正典。
最后,联系到救赎历史,简述一下作为新圣约启示中介的使徒们所起到的四个重要作用[20]:
1)他们是基督有权柄的代表(约13:20;林前14:37-38);
2)他们是教会的根基(太16:18——彼得的宣告;弗2:20);
3)他们最为重要的任务,便是为基督的位格及一次性完成的救赎之工作见证(约15:26-27;徒1:8);
4)他们有意要为教会存留使徒见证,在使徒离世之后,这些见证由新约正典所证实。
伽芬(Gaffin)在描述使徒性与正典性时这样说道:“由此,使徒见证不仅仅是个人的证言,而是一种有着绝对无误的权柄,且具有法律约束的作证……这种见证体现了正典性原则,为新的正典提供了矩阵(matrix),而新的正典是与旧约中恩约启示所并列的一个新启示体系。”[21]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持守的立场是:在公元一世纪、当这二十七卷正典经卷作为圣灵“所默示的”话语被撰写下来的时候,新约正典便产生了。正典的绝对权威性在于其神圣起源。正典是自证为真的。教会认可正典的历史过程,仅仅是在为这二十七经卷的正典性作见证,而不是在证明或决定这些经卷的正典性。神的救赎之工已经藉着基督圆满成就,新约的启示也由此完成了,正典就已成为不容更改的,即正典已经完成。
作者简介:
蒋虹嘉,毕业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之前也参与基督教书籍的翻译事工。
[1] M. J. Kruger, “Deconstructing Canon: Recent Challenges to the Origins and Author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Writings,” in Did God Really Say? ed. D.B. Garner (New Jersey: P&R Publishing, 2012). [2] M. J. Kruger, Canon Revisited: Establishing the Origins and Author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Books. (Wheaton: Crossway, 2012). [3] A. C. Sundberg, “Towards 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New Testament Canon.” SE 4 (1968): 452-61. [4] H. Lundhaug, “Canon and Interpretatio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Canon and Canonicity: The Formation and Use of Scripture, ed. Thomasson (Copenhagen: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2010). [5] L. M. McDonald, The Biblical Canon: Its Origin, Transmission, and Authority (Peabody, MA: Hendrickson, 2007). [6] Von Harnack, A Hisotry of Dogma, vol. II (New York: Dover, 1961). [7] P. Ricoeur, “The ‘Scared’ Text and the Community,” in The Critical Study of Sacred Texts, ed. W. D. O’Flaherty (Berkeley: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1979). [8] M. Webe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Boston: Beacon, 1993); W. Bauer, Orthodoxy and Heresy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1). [9] L. M. McDonald, “Canon” in Dictionary of the Later New Testament and its Developments, ed. P. M. Ralph and P. H. Davids (Downers Grove: IVP, 1997). [10] H. Y. Gamble, The New Testament Canon: Its Making and Meaning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5). [11] H. Y. Gamble, “Christianity: Scripture and Canon” in The Holy Book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F. M. Denny and R. L. Taylor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5). [12] R. B. Gaffin Jr., “The New Testament as Canon” in Inerrancy and Hermeneutic: A Tradition, a Challenge, a Debate, ed. H. M. Conn (Grand Rapids: Baker, 1988). [13] McDonald, “Canon” in Dictionary of the Later New Testament and its Developments. [14] Kruger, Canon Revisited. [15] B. B. Warfield, “The Biblical Idea of Inspiration” in The Inspiration and Authority of the Bible (Phillipsburg, NJ: P&R, 1948), 148. [16]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钱曜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0),1:7。 [17]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1:7;《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1:5。 [18] Kruger, Canon Revisited, 200. [19] Kruger, “Deconstructing Canon,” 57. [20] Gaffin, “The New Testament as Canon”. [21] Gaffin, “The New Testament as Canon,” 176.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